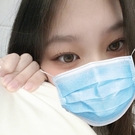小說名稱:[暴力虐待]販賣
(一)
9 月的哈爾濱,已經可以使人感到陣陣的寒意了,街上行人不多,湛藍的天上一群準備南遷的候鳥在城市的上空中追逐著最後的快樂,陽光從遠出斜斜地射來,這一切都在向人們轉達著秋的資訊。經過了上次的陣痛,萍(這�就簡稱為萍吧)對婚姻已徹底地失去了信心,她曾經深愛和信賴的男人在騙取了自己的感情後變得好賭和花心,整日在外私混搞女人,回家時通常都是一身的酒氣,稍有不順就拳腳相加。那次,丈夫又是在酒後回到了家�,為了3 歲的兒子上幼稚園的費用問題,萍觸怒了那個傢夥,拳頭象雨點般砸向這個不幸的女人。這次,她沒有再流眼淚,她對眼前這個男人已經由失望到了絕望,她決定離開他……
幾天後,萍如願以償地和他分了手,分手時,他說他很對不住這個家,對不住自己和孩子,萍對此甚麼也沒說,隨後,她將兒子託付給母親,決定一人到南方的朋友家去散散心。
“小姐,要票嗎?”幾個票販子在向萍兜售車票,臉上一副不懷好意的壞笑。單從萍的外表來判斷這個女人的話,誰也不可能會想到她曾經結過婚生過子,圓圓的臉,清澈透亮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豐滿的嘴唇總使人有想親一口的欲望,齊肩中長髮,身材不高,但很標緻,婚姻給了她少婦獨有的風韻,尤其那對奶子,把整個襯衣撐得滿滿當當,屁股渾圓有彈性,纖腰玉腿,白白的腳丫塗著紅色的指甲油,穿一雙白色高跟細帶涼鞋,真是個玲瓏美人。
“小姐,有去**的票,鴛鴦座!別等啦”。票販象蒼蠅一樣圍著萍轉個不停,“小姐,一個人啊?要不要我幫你拿行李啊,我們全套服務啊,呵呵”。萍狠狠瞪了票販一眼,向售票窗口走去。“後面的人別排了,近兩天的票全售完啦,別排啦,別排啦!”售票人員在大聲吆喝。真是倒楣,剛出門就這麼不順,萍顯得很沮喪。
“閨女,去哪兒啊?俺有車。”萍順著聲音擡頭望去,一個40多歲樣子的婦女微笑著問自己,“去*** ,你們是?”“閨女,別怕,俺們是****人,來哈爾濱送點貨,現在要回家了,想順路拉點客人掙點錢,你瞧著給點就行,反正不拉白不拉。”“可是……”“別可是啦,閨女,快上車吧,早點走早點到啊。”萍看著售票窗口還在擁擠的人群,心想,反正也買不到票,看她也不像壞人,走就走吧。
那個女人告訴萍,她叫雲,2 年前下了崗,和丈夫辦起了運輸公司,雖然辛苦,但日子過得還算不錯。說話間來到了一輛帆布蓬大卡車前,車�坐著一個精瘦的男人,可能就是雲的丈夫。
“安子,這閨女去*** ,正好順路。”“好嘞,上車”安子說罷,跳下了車,“閨女,來,咱到後面來”萍心中想,不會讓我坐在後面的車鬥�吧?雲好象看出了萍的心事,忙說:“閨女,這車雖比不上客車舒服,但也寬敞,將就一下吧,很快就到了。”萍琢磨著,反正也來了,總比再等2 天強,將就就將就吧。
車廂是用帆布大蓬蒙住的,蓬�是生鐵焊成的圍欄和門,雲帶萍上了車廂,說:“閨女,看你一個人在外也不容易,乾脆我陪你一起坐這�吧,咱們還可以嘮嘮磕。”車啟動了,萍打量著車廂,車廂很大,靠近駕駛室的部分堆放了好多大箱子,像是貨物,占了車廂面積的近一半,由於有帆布蓬,車廂�光線很暗,幾乎看不清箱子�裝的是甚麼。雲一路上不停地在訴說自己創業的艱難和經受的委屈,萍聽著聽著就不知不覺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汽車好象停了下來,萍在顛簸中被搖醒,雲已經不在車廂�了,她去了哪里?正在想著,車廂的帆布門被打開,外面漆黑一片,估計是晚上,這時上來2 個男人模樣的人,萍此時有中不祥的預感,她警覺地蹭的一下站了起來,還沒說話,其中一個男的就已經飛快地沖了上來,繞到身後扭住了萍的兩支胳膊,“你們幹甚麼?你們是誰?”萍大聲叫著。“救命!救命啊!嗚……嗚嗚。嗚……”聽見叫聲,另外那名男子用一塊毛巾狠命地塞進了萍的嘴�,萍感覺毛巾都已經被塞到了嗓子眼,一陣想嘔吐的感覺頓時湧來,可是嘴�被毛巾塞得滿滿的,即使感到噁心,也甚麼都吐不出來。毛巾塞好後,外面又被用透明膠帶圍著頭纏了七、八圈,這下想吐也吐不出來了。緊接著,一條麻繩從脖子後面搭到了前胸,順著腋下到了身後,在大臂、小臂上各纏繞了數圈後於背後將兩支手腕緊緊地捆住,這時,捆住手腕的麻繩不知怎麼被往上提了一下,萍的兩支手猛地被提到後背上,由於手在背後被高高吊起,萍只能努力地挺著她那圓潤豐滿的乳房,以減輕繩子對身體的壓力。“他們是甚麼人?我被綁架了?”萍在被捆的時候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這時,萍隱約聽見車下有人說話:“這個價絕對不行,這丫頭這麼俊,是塊好貨,我們好不容易才到手的……”聽聲音好象像是雲在說話。此時萍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原來碰上了人販子,她又急又氣,嗚嗚地發出絕望的呻吟,拼命地扭動已被捆得粽成了一團的上身。“別他媽亂動,再動我抽你”一個男人惡狠狠地說。萍流著淚,擡起頭望著那個男人,眼神�充滿了企求,她企求這些人能大發慈悲,放了自己,但他們根本不去理會到手肥貨心中感受。
過了一會,也許是車外的生意順利成交,車上的男人架起萍向外走去,在下車的一刹那,萍看見了雲,她的眼睛在一瞬間偷偷地避開了萍那充滿憤怒的目光。車外還有一名男子,樣子像30多歲,沒有車上那2 個男人那麼強壯,但也很結實,臉上清晰的有一條3 寸來長的刀疤,一雙小眯縫眼,望著就讓人膽寒。他們將萍從車上架下來後,車就開走了,最後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萍被2 個男人一左一右地架著,向一條小路走去,刀疤走在後面。萍這時才開始注意到周圍的環境,這�好象是靠近山村的地方,四周看不到一點燈光,遠處依稀可見大山的影子,一條土路不寬,蜿蜿蜒蜒地也不知伸向甚麼地方,身後不遠可能是公路,剛才就是從那�被押送下來的,坡度很大。
走了大概有半個多小時,刀疤對另外2 個人說:“是這條路嗎?怎麼不太像,我們停下來看看再走。”萍這時感到2 只胳膊和手臂已經麻的已經沒有知覺了,由於嘴被堵著,只能靠鼻子來呼吸,她深深地喘著粗氣,在這樣幾個高大男人面前,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刀疤和1 個男的去前面探路,只剩下另外一個人在看守她,她在偷偷琢磨著怎麼逃跑,機會來了,萍趁那個傢夥小便的時候,一腳把他踹進了路邊的溝�,轉身拔腿就跑。萍穿著高跟涼鞋,很不跟腳,再加上身體被繩索緊緊捆住,掌握不了重心,剛跑出20多米,就被從後面趕上的男人抓住了,他拽著她的頭髮把她拖了回來,耳光重重地落在她的臉上,萍被打的眼冒金星,嗚……嗚地痛苦呻吟。“打死你個賤貨,看你還敢不敢跑……”
刀疤他們探路回來了,知道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後,他從包�拿出一副厚重的腳鐐仍在了地上,“給她帶上這個”
萍看著眼前這副厚重的腳鐐,心情只有用萬念具灰來形容了,這堆生鐵傢夥重量足有10多公斤,戴上它想擡起腿都覺得費勁,更別說還要走那麼遠的山路。想到這�,萍急得眼淚又要忍不住流出來了。
“大哥,我看不用帶這個吧,我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那妞帶著它得甚麼時候能走到啊?”“那也比到手的鴨子飛了強,別他媽廢話了,快給她帶上。”刀疤催促著同夥快點幹活。只聽卡嚓、卡嚓兩聲沈悶的金屬聲響,腳鐐被死死地銬在了萍的一雙腳腕上,萍想到再無逃脫的機會,只能任由眼前這幾個兇惡男人的擺佈,今生也許再也見不到心愛的兒子和慈祥的媽媽,眼淚順著臉龐流了下來。
夜色下,4 個人影沿著山間小路緩慢地向遠方移動,萍被兩個男人架在中間,拖著沈重的腳鐐,踉踉蹌蹌地向前走著。小腿酸脹的好象已經不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了,腳腕早已被鐐銬磨掉了一層皮,露出了鮮紅的嫩肉,疼得叫人鑽心。人販子真是狠毒,對付這樣一個柔弱的女人居然還使出這麼殘酷的辦法。萍真後悔剛才為甚麼要逃跑,以至遭來更加嚴厲的束縛。
“嗚……嗚,嗚……”萍實在是忍受不了了,她此時寧願去死,也不想再受這樣的折磨。“大哥,這妞好象要說話”“別理她,趕路”刀疤沒有理會萍的示意。“嗚……嗚”萍一邊呻吟,一邊死命地掙扎。“他媽的,這妞真他媽不安分。把她嘴�的毛巾拿出來,看這婊子想幹甚麼?”刀疤終於讓萍搞的有些沒耐心了。
“哇……哦”毛巾剛一拔出來,萍就忍不住要嘔吐。“幾位大哥,我求求你們了,我不跑了,你們把我腳上的鐵鏈拿掉吧,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也不叫,別再用毛巾堵我的嘴了,我氣都快喘不上來了。”萍用近乎哭的腔調哀求刀疤一夥。
“閨女,實話告訴你,這腳鐐的鑰匙我們也沒有,要到了買家那�才能打開,你就將就將就吧,誰叫你不老實呢,至於嘴嘛,等天亮進了山�再說,堵上。”
還沒等萍做出回應,毛巾又重被塞進了嘴�,外面又纏上幾圈膠條。萍拼命扭動繩索捆綁下凹凸豐腴的身體並嗚嗚地叫著以表示強烈的抗議。“他媽的,你還真夠倔啊,不給你緊緊皮,你是不長記性啊,來,把她給我吊起來。”刀疤惡狠狠地說到。
幾個人三下兩下把萍拽到小路邊一棵大樹下,刀疤掏出麻繩,一頭繞過碗口粗的樹枝,另一頭系在萍後背麻繩的交叉處並打好了結。萍感到後背一緊,一股向上的力量將自己拽了起來,由於身體的重量,身上的麻繩深深地勒進了肉�,越來越緊,她感覺快要透不過氣來,身體在一點一點地上升,萍用腳尖努力地夠向地面,但結果是離地面越來越遠。萍整個人被懸空吊在了半空中,腦袋無力地垂在胸前,一頭秀髮披散在臉側,兩隻嫩足在空中做著無用地掙扎,體重加上腳鐐的重量,萍的表情痛苦萬分。
刀疤拿著皮帶,站在萍的下麵,幸災樂禍地觸摸著勒在萍身上的繩索,突然一揮手中的皮帶,重重地抽在了萍的身上,“嗚……阿。”萍擡起頭大聲呻吟著,皮帶開始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萍的大腿、屁股、乳房這些女人最敏感的部位,萍的額頭滲滿了豆大的汗珠子,嘴中的呻吟聲也逐漸變成了來自鼻子的哼哼聲。由於疼痛,萍失禁了,尿液順著大腿滴到了地上,腳下的黃土被滲失了一大片。
刀疤他們打了半天也打累了,坐在地上抽起了煙。“大哥,這�離山口不遠了,進了山,誰也別想找到我們了,等到了石老二家,你還不好好疼疼這妞?哈哈哈哈。”“呵呵,等大哥我爽完了,你們哥倆也有份。”刀疤對同伴說到。原來,石老二是他們的同夥,就住在這深山�,是他們販賣女人的中轉站,通常他們把綁來的女人先帶到石老二的家�,在這�等待買主的到來和進行交易,買主再把買來的女人從這�運走。人販子在販賣婦女時,都會將女人糟蹋一番,一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獸欲,二來是為了徹底摧毀女人的心理防線,任由自己擺佈。
萍被抽打得暈死了過去,涼颼颼的夜風將她吹醒,麻繩捆吊的疼痛使她不自覺地哼哼著,胸前的襯衣扣已不知甚麼時候被解開了,一對白皙豐滿的奶子在繩索地包圍下鼓鼓地向上翹著,上面依稀可見抽打過的鞭痕。刀疤見她醒了過來,掐滅手中的煙頭,讓兩個同伴把她放了下來,繼續朝著黑夜走去。
天空泛起了魚肚白,萍已經被押送了一個晚上,腳碗撕裂般的疼痛也已被麻木所代替,現在已經是在深山�了,除了可以聽到自己走路時鐵鏈與石塊的撞擊聲和人販子不時地私語,就再也聽不到來自外界的其他信號了。在這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山�面,一個人是很難走出去的,人販子把這個地方作為交易的中心,也真是煞費苦心。真不知曾經有多少女人從這�被販賣到別的地方。萍擡頭向山上望去,正好趕上朝陽從山的那邊升起,陽光透過樹林劃出萬道美麗的光線灑在自己的臉上,似希望之火重新點燃,刹那間對自由的嚮往傳遍全身。“我決不能被他們賣掉,我一定要找機會逃跑,就算是爬,我也要爬出去。”萍暗自思量。有了昨天晚上的教訓,萍對這次的逃跑計畫考慮得非常慎重,如果再失敗的話,後果……再者,現在不僅上身手臂被繩索緊緊地捆著,而且還戴著近30斤的腳鐐,並且腳上穿的還是一雙高跟涼鞋,在這樣的地形�行走,是困難且緩慢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先從人販子的視野中消失,然後再尋找出路。可是,這麼長的時間從哪里來呢?要等待機會,耐心地等待。想到這�,萍感到自己仿佛又看到了自由的曙光,身上的疼痛已不知不覺好了許多。
雖然是在山�,但晌午的驕陽依然能把趕路的人曬得汗水淋漓,刀疤的兩個同夥還要一左一右架著一個手腳被束縛的女人,與其說是架著,不如說是擡著,萍在繩索重鐐的關照下怎能像常人一樣走路?這兩個傢夥被累的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大哥,咱們一個晚上都沒有休息,現在安全了,也該找個落腳的地方好好歇歇了,等下午涼快點再趕路吧。”一個傢夥終於忍不住了。刀疤擡頭看了看炎炎烈日,對同伴說:“轉過前面有個瀑布,下面有水塘和平坦的石頭,那�可以落腳。”
果然沒走多遠,就聽見了水流從高處傾瀉飛濺的聲音,一條瀑布出現在面前,下面聚成一汪清澈見底水塘。一見到水,幾個人都興奮得恨不得馬上跳進去涼快涼快。萍被捆在水塘邊的樹上,看著刀疤他們毫無掩飾一絲不掛地在水塘�洗澡。“大哥,給那妞也洗洗吧。”“好啊,我還沒給女人洗過澡呢,哈哈哈。”說罷,幾個人躥上岸,把萍帶到水塘邊,用刀子割掉了她的衣服。一個全身赤裸,被麻繩和鐐銬捆綁著的美女呈現在了眼前,萍赤身裸體地站在三個男人面前,任由他們淫穢的目光上下打量,羞辱得無地自容。刀疤一把將她抱了起來,走進了水塘,手在她的乳房、蜜穴�不停地搓揉。“嗚……恩”萍呻吟了起來,不知不覺下身竟流出了蜜水。麻繩因為受水的浸泡,一下子收緊了不少,萍一點都掙扎不得。刀疤就勢把陽具插進了萍的私處,在水中大力地抽插了起來,岸上的傢夥看著他抱著那女人在水中一起一落地快活了起來,心中早已癢得受不了了,紛紛握住了自己的老二開始自慰。刀疤見了,嘿嘿一笑,把萍放在了岸邊,對著她的臉握著陽具上下搓動,一股粘稠的精液噴射在萍的臉上,那兩個傢夥也不甘示弱,前後也將精液射在萍的嘴上、眼睛上。
折騰夠了,刀疤他們歪歪斜斜躺在石頭上打起了午酣,萍躺在岸邊的石頭上,尋思著怎樣逃跑,眼下的機會難得,刀疤他們走了一夜,一個個累得筋疲力盡,趁他們現在剛睡著,此時不跑,更待何時。想到這�,萍悄悄挪動了一下身體以做試探,“嘩啦,”一聲鐐銬碰撞地面的聲響嚇了萍一大跳,不過那幾個人好象絲毫沒有察覺,可能是瀑布飛濺的水聲幫她掩飾了不少動靜的緣故。
萍的膽子大了起來,她開始嘗試從地上坐起來,首先她必須趴在地上,然後讓膝蓋和頭著力,使自己能跪起來,這期間還要儘量保持不讓腳鐐發出太大的聲響。經過幾次努力,她成功的跪了起來,剩下的就是站起來悄悄地走出去了,萍幾乎不敢呼吸了,她慢慢地站了起來,一點一點向外面挪動著腳,“噹啷”腳鐐響亮地碰到了一塊突出的岩石,萍感覺心快從嗓子眼�跳了出來,呆呆地立在了那�。
刀疤他們睡得很死,沒有被響聲吵醒,也許他們認為在這樣的地方,一個被束縛著的女子是無法逃出去的吧。萍站了半晌,確信他們沒有察覺後,一點一點地向樹林挪去,終於,她慢慢遠離了他們的視野,可以大膽地向前走去。
腳鐐死沈死沈,腳腕疼得難以忍受,萍一瘸一拐地拼命向前走著,能夠得到這樣的機會,再大的痛苦又算得了甚麼。由於緊張,萍感到腳下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緊接著整個人向前撲了過去,摔在了地上,原來是一段枯枝纏住了腳鐐,費了半天勁才把腳鐐從樹枝上弄下來。萍打算把捆住手臂的麻繩和堵在嘴�的毛巾弄出來,她找到一塊岩石,背靠著它開始磨繩子,可是剛剛被泡過水的繩子又緊又滑,磨了半天也沒見效果。手腕被勒出了血道,疼得鑽心。萍心急如焚,這樣下去,還沒跑多遠就會被發現追上,那可就真的完了。正在這時,遠處傳來了簌簌地腳步聲,萍驚得差點暈了過去,刀疤他們已經追上來了。
還未來得及仔細想,萍就已經看見不遠處樹林中人頭攢動地向這個方向跑來。“他們來的可真快”萍心想。眼下跑是不可能了,藏?又沒有能夠完全隱蔽的地方可以藏身。也管不了這麼多了,萍就勢滾到了草叢中,全身趴在了地上,大氣也不敢喘一喘。剛剛藏好,刀疤他們就從眼前跑了過去。好懸!差一點就要被抓住了,萍暗自慶倖。
可腳步聲過去沒多遠就停了下來,萍剛剛鬆弛下來的神經又一下子緊繃了起來,難道他們發現我了?透過草叢,萍看到那幾個人在低頭看著甚麼………。。
刀疤果然是個狡猾的人販子,他順著萍在地上留下的腳印一路追來,到了這�,腳印沒有了,這說明她就在附近。因為萍穿的是高跟鞋,在這樣鬆軟的土地上留下的痕跡很容易辨認。萍絕望地閉緊了眼睛,此時的命運只有由上天來安排了。刀疤他們也很快就發現了草叢背後捆綁在那�的萍。“哈哈哈哈!老天真是他媽的心疼咱們兄弟,沒有讓到手的肥鵝飛掉,兄弟們!把這個賤貨給我拖出來!”二個男人過去一左一右把萍從草叢�架到了刀疤面前,“啪、啪……”刀疤用力抽打著萍的臉龐,“你個臭婊子,我叫你跑!”刀疤一邊罵一邊不停手地抽打著萍。
“這婊子真他媽的夠野啊,五花大綁戴著腳鐐還不塌實”一個同伴說道。萍倔強地擡起頭,怒視著眼前的人販子,雖然嘴�發不出聲音,但是她還是嗚嗚地表示著自己的不屈服和抗議。刀疤此時心中感到眼前的這個女人可不象以往那些畏懼暴力、無比順從的被賣女,她有思想,還有膽量。如果不嚴加看管,早晚必受其害。想到這�,刀疤停止了抽打,讓二個同伴帶著她繼續趕路,為防意外,刀疤讓同伴把萍駟馬攢蹄捆好,找了個粗木棍,從萍背後和腳上的繩子穿過去,然後擡著她走。萍整個身體反弓著被吊在一根木棍上,痛苦異常,兩隻肩胛骨向後向上高高撅起,手腕和腳碗撕裂般火辣辣的疼。由於身體反弓加上嘴�還塞著毛巾,萍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窒息,喘不過氣來,走了沒多遠,豆大的汗珠子順著雙頰滴答滴答留到了地上。更可氣的是後面那個擡她的傢夥手還不老實,時不時地撫摩幾下她光滑的大腿和嫩足。山路崎嶇,萍的身體在空中上下顛簸、左搖右擺,每一次搖擺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萍忽然感到下面一熱,一股熱流穿透了絲襪順著大腿根流了出來,小便失禁了。這可把後面那個傢夥樂壞了“快看呀!這騷娘們尿了!流了一地,哈哈!”“應該在她的逼上上把鎖,省得她亂撒尿”前面的傢夥說。萍想到自己被人像擡畜生一樣的吊在棍子上,還遭到了如此嘲笑,屈辱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順著雙頰留了下來,落在了路邊的花瓣上。
正在走時,刀疤突然停下了腳步。“怎麼不走了?大哥?”“前面好象有人。”“不會啊,這深山老林�,怎麼會有人來呢?”“看那……”順著刀疤指的方向,對面果然有兩個人向這�走來,他們好象也注意到了這邊,站在那�眺望。
“怎麼辦?大哥,要不要躲一躲?”刀疤眯了一下小眼,沈思一下說:“不,躲反而會被懷疑,迎過去!”“可是這……”“一會我來應付”說罷,幾個人加快了步伐,朝對面的人走去。不一會,兩撥人就相遇了,刀疤上下掂量著對方,從裝束上看,像是進山打獵的。“兩位是來搞山貨的?”刀疤笑咪咪地說。“是啊,這季節正是好時候,山貨比較多,幾位是?呦!這姑娘是??”“咳!別提了,她是我親妹子,逃婚!剛被我們抓到,不願跟我們回去,尋死覓活的,不這樣綁著制不住她,爹媽在家都快急瘋了!”刀疤回道。“哎!這姑娘也夠可憐的,”“沒法子啊,山�人嫁閨女的聘禮能養活一家人,如今人家的聘禮收了,人跑了咋交代啊。”“哎!你們也不容易啊,行了,你們還是趕緊趕路吧。”萍聽到這些,拼命地掙扎著,嗚嗚地呻吟著,希望眼前這兩個獵人能識破人販子的詭計救自己出去,可一切都是徒勞,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希望從面前漸漸消失,而毫無為力。
將近傍晚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密林深處的一間老房子前,刀疤止住同伴,隻身一人進了屋,半袋煙的工夫,同兩個人一起走了出來,一人是一位老者,相貌醜陋,微有駝背、鑲一嘴金牙,另一男子滿臉橫肉,身材高大魁梧。刀疤很尊敬這位老者,據說此人原先是山�的鬍子,姓袁,人稱袁金牙,生性殘忍狡詐,曾經稱霸一方,打一手好槍,當年剿匪時,死在他槍下的解放軍官兵就有不少,其中還不乏歷經了幾次大戰役的戰鬥英雄。這之後被政府通緝多年在逃,無處藏身,只好躲進了這深山老林,幹起了販賣婦女的勾當,旁邊的大個子是他當年和城�一個很有名氣的窯姐所生,從他滿臉的橫肉和陰險的目光可以看出此人的兇殘也絕不在其父之下。因為這�地形複雜,人跡罕見,所以多年以來,父子倆的人口生意越做越好,慢慢竟變成了中國向境外輸出妓女和性奴隸的主要來源地。綁來這�的姑娘,大部分被轉賣到俄羅斯海參威的妓院充當妓女,也有東歐一些地方的妓院老闆來這�挑選上好的貨色,然後這些女人要被輾轉幾個國家長途販賣,最遠的曾經被賣到了巴拿馬的妓院或者是衣索比亞的性奴隸市場,經過這麼多人倒手,最後的價格也是不菲的。
袁金牙看著吊在木棍上早已筋疲力盡的萍,對刀疤說:“這妞你想賣多少錢?”“哦!呵呵!價錢好說,價錢好說,就是不知您老看得上不?”“你小子少他媽來這套,3000塊,你把人放這,否則就走人。”“老太爺!您高擡貴手,我們哥幾個這一路不容易啊,中間還差點讓這婊子給跑了!這妞盤子亮,我們收她的價也不止您這些個呀。”“4000塊,一口價,我他媽做一次好人,多那1000你們兄弟去喝酒吧。再給我還價,我可要翻臉啦!”刀疤聽罷連忙點頭答應,4000塊成交了。袁金牙心中竊喜,其實他明白:就眼前這塊肥嫩的肉,能好好敲上毛子一筆,所得的價錢又何止4000?
萍迷迷糊糊覺得被人從木棍上放了下來,身上的繩子和腳鐐也被解開了,2只胳膊像折了一樣無力地垂在兩側,已經不聽使喚了,這可是她2 天一夜以來第一次被鬆開束縛感受手腳的自由。但是馬上大個子走了過來,手�提著一副厚重的鐐銬,鐐銬很奇特,首先是套在脖子上的金屬圈,在卡嚓一聲鎖死後一條鐵鏈連著一副大約15毫米厚的手銬將萍的雙手鎖死,手銬下面的鐵鏈連著腳鐐,腳鐐也很厚重,兩腳間的鐵鏈粗厚沈重,但不長,有30釐米左右。大個子一邊給萍鎖上鐐銬,一邊對身邊的刀疤說這副鐐銬是在俄羅斯定做的,材料經過了特殊的處理,鋼挫和電鋸打磨根本就無法打開這種鐐銬,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鑰匙,另外還有一種時間限定的功能,通過脖子上的項圈設定鐐銬自動打開的時間,在這以前,即便用鑰匙,也無法打開鐐銬。一般他們在給被賣女鎖上這種鐐銬時都採用時間設定的方式,這樣比較安全。時間可長可短,最長可設定五年。說罷,他將萍的時間設定到一年,鎖死了開關。
萍無力地擡起手,撫弄了一下淩亂的發際,鐐銬發出清脆的金屬撞擊聲,隨即,大個子推搡著她向屋�走去,而袁金牙和刀疤在一邊忙著點錢算帳。進了屋子,發現�面很大,正堂兩邊各有間房,轉過正堂後面還有一間,像是儲藏室,大個子挪開屋子內的一個櫃子,在牆上扳動了一下,忽然只見牆上打開了一扇石門,原來這�面還有密室!萍被大個子推進石門,進石門後是向下的臺階,然後拐彎進入走廊,走廊盡頭一扇厚鐵門緊緊鎖著,�面泛著微弱的燈光。打開鐵門後是一個大房間,房間被鐵柵欄分成了四五個囚室,中間是過道,大個子打開其中一個囚室,把萍推了進去,返身鎖上門,走了。隨著門鎖卡嚓卡嚓的落響,一切又恢復了寂靜。萍恐懼地蜷縮在牢籠的一角,心中的噩夢在不斷延續……
四周一片寂靜,除了萍偶爾動動身子,鐐銬發出的金屬撞擊聲,就再也沒有任何聲音了。萍的思緒在寂靜中飄得很遠,她想起了在家的時光,想起了孩子、母親甚至是前夫。比起現在的處境,那些過去看似的不幸仿佛也變的充滿了人情。萍開始後悔自己的倔強和衝動,如果換做一個溫順的女人,也許現在還在過著雖有煩惱但還平靜的清淡生活。那也要比成為別人的一件物品,任由發落強得多。現在這個樣子,生還不如死。想到這�,萍留下了絕望的眼淚。
販賣(二)
經歷了一路的痛楚折磨,萍不知不覺地沈沈睡去,直到鐵門發出沈重的撞擊 聲將她驚醒。進來的是大個子,從他臉上不懷好意的壞笑,萍很快意識到下面將要發生什麼。她出於本能地縮緊了身體,向後面靠去,臉上的表情驚恐無助。
大個子也沒有多餘的廢話,很利索地把萍身上的衣服撕了個精光,只剩下一個裸露著豐腴侗體、戴著手銬腳鐐的女人躺在地上。大個子一把抓住萍的頭髮,將她拽起來跪在地上,她那柔軟的嘴唇正好對著褲子�漲大的陽具。陽具深深地插進萍 的喉�,在那�放肆地四處遊動,令萍感到陣陣的噁心,大個子有些不高興,抓住萍頭髮的手猛然向後下拽了下去,萍的頭一下子被動地向後仰去,目視著陽具從上面深深地插了下來……正在大個子對萍進行蹂躪的時候,鐵門的一側站著一個人,袁金牙。他無意中看到了眼前的這一幕,又默不做聲靜悄悄的走開了。
深夜,袁金牙將睡夢中的萍叫醒,親自把一副2MM 厚生鐵打制的貞K 帶鎖在了她的身上,他是不希望眼前這個女人在交易前發生什麼麻煩的事情。
許多個日日夜夜,萍就在這昏暗潮濕的地下牢籠中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就像一隻被人圈養牲畜,饑餓和寒冷侵襲著全身上下,見到主人手�的硬饅頭和稀飯像看到了一桌子的美味佳餚,拖著鐐銬的身體緊緊貼在冰冷的鐵柵欄門上用乞求渴望的眼神望著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什麼尊嚴、廉恥、女人的矜持、羞澀通通已不復存在了,暴露出了作為人最簡單的需求。萍為了儘快獲得食物有時會被要求擺弄一些淫蕩、猥褻的肢體姿勢和舞蹈,時間久了居然也能像夜總會的裸舞女郎那樣搞出各式各樣勾人魂魄的姿勢了,袁金牙真是老到,他已把當初那個倔強、桀驁的女人訓練的服服貼貼、百依百順了。除此,萍每隔一段時間會被注射一種藥物,據說,這種藥物可以長久保持女人膚質具有彈性和光澤,同時可以有效改善體形,它�面的藥物成分會使乳房發育的很豐滿,腰間的脂肪向下移動,臀部的脂肪會進一步變厚,達到豐乳肥臀。泰國和東歐的妓院經常為妓女注射這種藥物以保持她們迷人的身材和漂亮的臉蛋。
一天夜�,萍恍惚中聽到一陣碰撞聲,一個年輕女子被大個子連推帶搡押了進來,女人上身被麻繩緊緊地綁著,腳上帶著一副黑漆漆的腳鐐,嘴上一條布帶纏在腦後,�面鼓鼓囊囊,像是塞滿了東西。那女人似乎很倔強,不停地在掙扎和反抗,大個子打開萍對面的牢房,把她拖進去剛要轉身縮門,女人從後面向他撞來,險些將他撞倒。大個子一下被激怒了,他怒不可泄地抓住那女人的頭髮,把她拽到屋子中間,掏出一條繩子系在她後背,再穿過屋頂的鐵環,用力把她吊了起來,然後罵罵咧咧地走了。萍這時才來得及仔細打量眼前的這個女人,她看上去很年輕,身材勻稱,凹凸有致,一頭長髮披散在臉前,遮住了垂在胸前的面部,及腳腕的連衣長裙使人顯得修長,裙子上很多地方都已經襤褸破損,可見一路上也是受盡磨難,一雙白色細帶高跟涼鞋包裹著一雙白嫩修長的玉足,腳趾上左右交叉著兩條細細的帶子,拇指在鞋尖向上微翹著,其他腳趾依次向後排列,指甲上塗著黑紫的指甲油。女人被吊的很痛苦,每扭動一下,身體都會在空中旋轉半圈,那副腳鐐看上去也不輕,女人的腳動也不敢動一下。萍幾乎是一晚沒有睡著,對面女人嘴�嗚嗚的呻吟聲讓她揪心。天剛亮,大個子就來到牢房,把那個女人從鐵環上放了下來,女人一灘軟泥似的倒在地上,大個子解開她身上的麻繩,換成了和萍身上一樣的鐐銬。
萍慢慢知道了那個女人叫曼,是個在校大學生,返校途中被人販子拐騙賣到了這�。曼是個清秀的女孩子,典型的江南美人,剛來的幾天�終日以淚洗面,不吃不喝,沒多久也就平靜了下來,現在不時的和萍聊一聊自己的身世和經歷,形同姐妹。
由於藥物的作用,萍和曼的奶子發育的越來越豐碩,現在每天都要從�面擠出許多奶水,否則漲痛得使人受不了,擠出的奶水都被大個子收走了,如果數量不夠就會被罰挨餓,所以除了吃飯聊天,姐妹兩人大多數時間都在用戴著手銬的雙手努力地擠奶以求達到數量。
這一天,牢房的鐵門打開後,進來的是袁金牙,在他身後還跟著一個身材高大一臉鬍鬚的洋人。萍和曼感覺到今天的氛圍不對,姐妹倆相互對視了一下,怔怔地望著來人。“強森先生,請您仔細過目,我對您的承諾是絕對不會有偏差地,哈哈哈“袁金牙疵牙咧嘴地對那個毛子說。”恩,我喜歡的類型,2 個我都要了哈哈哈哈,袁老闆,你出個價錢吧。“毛子說。”好!既然強森先生這麼識貨色,我袁金牙交你這個朋友,30000 元!怎麼樣?“”NO NO NO,袁老闆,你在和我開玩笑,這樣的貨色你幾千塊就可以買到了。“”強森先生,話不能這樣講啊,我買了她們,還要養活她們啊,在她們身上花的錢難道讓我白花啊“”這樣吧,20000 塊,我們成交OK?“”不行,最少也不能低於24000 元,否則我去找其他買主“袁金牙假裝沒有耐心了。”好吧,袁老闆果然是會做生意,哈哈,我們成交,明天我的人過來發貨。“”呵呵,痛快!今晚我請強森先生嘗嘗我們山�的野味,請!“
萍和曼目瞪口呆地聽完兩人的商品買賣交易,而交易的商品就是自己的肉體,她們不知到明天自己將會被作為商品運到什麼樣的地方去,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屋子�一片寂靜,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過了許久,鐵門被打開了,大個子提著一個大皮包走了進來,他先打開萍的牢門,沖著萍嘿嘿的笑了兩聲,說“還真捨不得你呢,心肝。”說完他從包�拿出一個類似於噴槍的東西,只不過前部是幾排密密麻麻的針尖組成的圓圈內有個倒A 字的圖案,原來這是一個專門為妓女或性奴隸打上標識的紋身機,針頭組成的圖案區分著奴隸所從屬的主人。隨著萍的幾聲慘叫,大個子在她的乳房、臀部打上了印記,並熟練地為她上了一次性鋼制乳環、臍環和陰環。曼也被同樣的裝扮了一番。
販賣(三)
大個子做完這一切,很滿意地走了出去,剩下兩個被標上標籤等待出售的女人。被刺過記號的地方火辣辣得疼,穿了環的皮膚立刻腫脹了起來,萍用帶著手銬的手輕輕地撫摩著痛處,試著想把鋼環取下,但鋼環合上後卻沒有一絲縫隙,就像是整體鑄造的一樣。曼則在一旁不停地抽泣,片刻後,她對著萍說:“萍姐,我不想被他們賣到國外,我們該怎麼辦?你快想想辦法啊。“萍看著眼睛哭得略微紅腫的曼,嘴角閃出一絲無奈的微笑,她何嘗又希望自己被人賣到遙遠的異國他鄉,遠離甚至永遠的與親人分別呢,可是,自從被販賣的那一天起,自己就從沒放棄過逃走的念頭,一次次的逃走,一次次地被抓回來,身體自由受到嚴厲的限制,手銬、腳鐐、鐵牢、身上的標記……在這深山老林�,就算跑又能跑多遠?跑到哪里去?自己早已認命了,可是曼還很年輕,她有理想、有前途、這樣被毀了的確令人感到惋惜,每當看到她那雙水汪汪、略帶天真的大眼睛,萍都會覺得心疼。作為大姐姐,自己還沒有為這個小妹妹做過什麼,哪怕是為她挽挽發際,萍心�在想:如果將來有機會,一定會盡力幫助她。
這個晚上,姐妹兩人誰都沒有睡好,寂靜的夜晚,牢房�輾轉發出的金屬鐐銬與地面的撞擊聲格外刺耳。天亮的時候,強森的人在大個子的帶領下,打開牢門走了進來,這是一群訓練有素的打手,個個高大彪悍,兇殘的眼神令人望而生畏。幾個人進來後不由分說,分別把萍和曼從牢房�拖了出來,在那麼多男人面前,兩個赤身裸體,鐐銬加身的女人既驚恐又羞澀,她們很快被人架著來到了地面的空場,萍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外面的空氣和陽光了,她閉著眼睛努力地呼吸著
……外面的溫度很冷,好象已經是隆冬了,萍想著自己被關進去的時候還是初秋,算來也應該有好幾個月了,這幾個月,不但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身體也從原來的柔美、勻稱變成了現在的豐腴,一對碩大的奶子在胸前晃來晃去,上下起伏,乳頭上的鋼環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細腰下肥碩的臀讓人看了就想去淩虐。曼也從剛來時的苗條修長變得越發豐滿結實,兩隻奶高高地聳立在胸前,紅潤的乳頭上還掛著未幹的奶水。屋外的空地上,袁金牙正在遠處和強森私語,大個子陪著4 個打手一左一右的架著萍和曼,不遠處樹林栓著7 、8 匹馬,有2 個人正
在從馬身上往下搬東西。他們搬的是厚重的木箱子,這箱子長1 米寬60高1米,箱子�面實際上是鋼條焊成的籠子,人放進去只能保持坐著或者跪著的姿勢,在箱子的一側,有個10CM見方的洞,是通風用的。
袁金牙用密碼打開了姐妹兩人身上的鐐銬,但馬上就被打手們用牛筋緊緊地反捆了起來,兩隻手被高高的吊在背後,並另外加了一副手銬。手銬上接一條繩直接從肩膀繞到前面分別系在2 個乳頭上的鋼環�。牛筋的特點是被捆的人越掙扎就會感到越緊,尤其是碰到水就會緊縮。姐妹兩人本來就豐滿的身體讓牛筋這麼一勒,更加凹凸有致,呼之欲出了,腳上的腳鐐被換成了30斤重鐐,而且是用母釘釘死了的,釘的時候把兩個女人疼得眼淚花花直流,3 個大漢一個掄錘,兩個摁著費了半天勁才算把腳鐐釘好。接著還要被戴上口鎖,口鎖是鋼制環形的,可以圍繞頭部嵌在嘴上,在腦後鎖死,嘴部有硬質橡膠口球,隨著口鎖的鎖死,口球會全部進入口出,打開氣閥,口球開始在嘴�充氣,以達到把嘴全部塞滿不留一絲空隙,使帶口鎖的人不能發出聲響。最後,萍和曼分別被人擡進了箱子,腳鐐被用鎖固定在箱子�的鋼柵欄上,當箱子蓋蓋上鎖死後,透過側面的通風洞,鋼柵欄後面一雙無助絕望的眼睛在流淚,她們開始踏上了通往性奴生活的道路。
9 月的哈爾濱,已經可以使人感到陣陣的寒意了,街上行人不多,湛藍的天上一群準備南遷的候鳥在城市的上空中追逐著最後的快樂,陽光從遠出斜斜地射來,這一切都在向人們轉達著秋的資訊。經過了上次的陣痛,萍(這�就簡稱為萍吧)對婚姻已徹底地失去了信心,她曾經深愛和信賴的男人在騙取了自己的感情後變得好賭和花心,整日在外私混搞女人,回家時通常都是一身的酒氣,稍有不順就拳腳相加。那次,丈夫又是在酒後回到了家�,為了3 歲的兒子上幼稚園的費用問題,萍觸怒了那個傢夥,拳頭象雨點般砸向這個不幸的女人。這次,她沒有再流眼淚,她對眼前這個男人已經由失望到了絕望,她決定離開他……
幾天後,萍如願以償地和他分了手,分手時,他說他很對不住這個家,對不住自己和孩子,萍對此甚麼也沒說,隨後,她將兒子託付給母親,決定一人到南方的朋友家去散散心。
“小姐,要票嗎?”幾個票販子在向萍兜售車票,臉上一副不懷好意的壞笑。單從萍的外表來判斷這個女人的話,誰也不可能會想到她曾經結過婚生過子,圓圓的臉,清澈透亮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豐滿的嘴唇總使人有想親一口的欲望,齊肩中長髮,身材不高,但很標緻,婚姻給了她少婦獨有的風韻,尤其那對奶子,把整個襯衣撐得滿滿當當,屁股渾圓有彈性,纖腰玉腿,白白的腳丫塗著紅色的指甲油,穿一雙白色高跟細帶涼鞋,真是個玲瓏美人。
“小姐,有去**的票,鴛鴦座!別等啦”。票販象蒼蠅一樣圍著萍轉個不停,“小姐,一個人啊?要不要我幫你拿行李啊,我們全套服務啊,呵呵”。萍狠狠瞪了票販一眼,向售票窗口走去。“後面的人別排了,近兩天的票全售完啦,別排啦,別排啦!”售票人員在大聲吆喝。真是倒楣,剛出門就這麼不順,萍顯得很沮喪。
“閨女,去哪兒啊?俺有車。”萍順著聲音擡頭望去,一個40多歲樣子的婦女微笑著問自己,“去*** ,你們是?”“閨女,別怕,俺們是****人,來哈爾濱送點貨,現在要回家了,想順路拉點客人掙點錢,你瞧著給點就行,反正不拉白不拉。”“可是……”“別可是啦,閨女,快上車吧,早點走早點到啊。”萍看著售票窗口還在擁擠的人群,心想,反正也買不到票,看她也不像壞人,走就走吧。
那個女人告訴萍,她叫雲,2 年前下了崗,和丈夫辦起了運輸公司,雖然辛苦,但日子過得還算不錯。說話間來到了一輛帆布蓬大卡車前,車�坐著一個精瘦的男人,可能就是雲的丈夫。
“安子,這閨女去*** ,正好順路。”“好嘞,上車”安子說罷,跳下了車,“閨女,來,咱到後面來”萍心中想,不會讓我坐在後面的車鬥�吧?雲好象看出了萍的心事,忙說:“閨女,這車雖比不上客車舒服,但也寬敞,將就一下吧,很快就到了。”萍琢磨著,反正也來了,總比再等2 天強,將就就將就吧。
車廂是用帆布大蓬蒙住的,蓬�是生鐵焊成的圍欄和門,雲帶萍上了車廂,說:“閨女,看你一個人在外也不容易,乾脆我陪你一起坐這�吧,咱們還可以嘮嘮磕。”車啟動了,萍打量著車廂,車廂很大,靠近駕駛室的部分堆放了好多大箱子,像是貨物,占了車廂面積的近一半,由於有帆布蓬,車廂�光線很暗,幾乎看不清箱子�裝的是甚麼。雲一路上不停地在訴說自己創業的艱難和經受的委屈,萍聽著聽著就不知不覺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汽車好象停了下來,萍在顛簸中被搖醒,雲已經不在車廂�了,她去了哪里?正在想著,車廂的帆布門被打開,外面漆黑一片,估計是晚上,這時上來2 個男人模樣的人,萍此時有中不祥的預感,她警覺地蹭的一下站了起來,還沒說話,其中一個男的就已經飛快地沖了上來,繞到身後扭住了萍的兩支胳膊,“你們幹甚麼?你們是誰?”萍大聲叫著。“救命!救命啊!嗚……嗚嗚。嗚……”聽見叫聲,另外那名男子用一塊毛巾狠命地塞進了萍的嘴�,萍感覺毛巾都已經被塞到了嗓子眼,一陣想嘔吐的感覺頓時湧來,可是嘴�被毛巾塞得滿滿的,即使感到噁心,也甚麼都吐不出來。毛巾塞好後,外面又被用透明膠帶圍著頭纏了七、八圈,這下想吐也吐不出來了。緊接著,一條麻繩從脖子後面搭到了前胸,順著腋下到了身後,在大臂、小臂上各纏繞了數圈後於背後將兩支手腕緊緊地捆住,這時,捆住手腕的麻繩不知怎麼被往上提了一下,萍的兩支手猛地被提到後背上,由於手在背後被高高吊起,萍只能努力地挺著她那圓潤豐滿的乳房,以減輕繩子對身體的壓力。“他們是甚麼人?我被綁架了?”萍在被捆的時候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這時,萍隱約聽見車下有人說話:“這個價絕對不行,這丫頭這麼俊,是塊好貨,我們好不容易才到手的……”聽聲音好象像是雲在說話。此時萍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原來碰上了人販子,她又急又氣,嗚嗚地發出絕望的呻吟,拼命地扭動已被捆得粽成了一團的上身。“別他媽亂動,再動我抽你”一個男人惡狠狠地說。萍流著淚,擡起頭望著那個男人,眼神�充滿了企求,她企求這些人能大發慈悲,放了自己,但他們根本不去理會到手肥貨心中感受。
過了一會,也許是車外的生意順利成交,車上的男人架起萍向外走去,在下車的一刹那,萍看見了雲,她的眼睛在一瞬間偷偷地避開了萍那充滿憤怒的目光。車外還有一名男子,樣子像30多歲,沒有車上那2 個男人那麼強壯,但也很結實,臉上清晰的有一條3 寸來長的刀疤,一雙小眯縫眼,望著就讓人膽寒。他們將萍從車上架下來後,車就開走了,最後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萍被2 個男人一左一右地架著,向一條小路走去,刀疤走在後面。萍這時才開始注意到周圍的環境,這�好象是靠近山村的地方,四周看不到一點燈光,遠處依稀可見大山的影子,一條土路不寬,蜿蜿蜒蜒地也不知伸向甚麼地方,身後不遠可能是公路,剛才就是從那�被押送下來的,坡度很大。
走了大概有半個多小時,刀疤對另外2 個人說:“是這條路嗎?怎麼不太像,我們停下來看看再走。”萍這時感到2 只胳膊和手臂已經麻的已經沒有知覺了,由於嘴被堵著,只能靠鼻子來呼吸,她深深地喘著粗氣,在這樣幾個高大男人面前,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刀疤和1 個男的去前面探路,只剩下另外一個人在看守她,她在偷偷琢磨著怎麼逃跑,機會來了,萍趁那個傢夥小便的時候,一腳把他踹進了路邊的溝�,轉身拔腿就跑。萍穿著高跟涼鞋,很不跟腳,再加上身體被繩索緊緊捆住,掌握不了重心,剛跑出20多米,就被從後面趕上的男人抓住了,他拽著她的頭髮把她拖了回來,耳光重重地落在她的臉上,萍被打的眼冒金星,嗚……嗚地痛苦呻吟。“打死你個賤貨,看你還敢不敢跑……”
刀疤他們探路回來了,知道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後,他從包�拿出一副厚重的腳鐐仍在了地上,“給她帶上這個”
萍看著眼前這副厚重的腳鐐,心情只有用萬念具灰來形容了,這堆生鐵傢夥重量足有10多公斤,戴上它想擡起腿都覺得費勁,更別說還要走那麼遠的山路。想到這�,萍急得眼淚又要忍不住流出來了。
“大哥,我看不用帶這個吧,我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那妞帶著它得甚麼時候能走到啊?”“那也比到手的鴨子飛了強,別他媽廢話了,快給她帶上。”刀疤催促著同夥快點幹活。只聽卡嚓、卡嚓兩聲沈悶的金屬聲響,腳鐐被死死地銬在了萍的一雙腳腕上,萍想到再無逃脫的機會,只能任由眼前這幾個兇惡男人的擺佈,今生也許再也見不到心愛的兒子和慈祥的媽媽,眼淚順著臉龐流了下來。
夜色下,4 個人影沿著山間小路緩慢地向遠方移動,萍被兩個男人架在中間,拖著沈重的腳鐐,踉踉蹌蹌地向前走著。小腿酸脹的好象已經不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了,腳腕早已被鐐銬磨掉了一層皮,露出了鮮紅的嫩肉,疼得叫人鑽心。人販子真是狠毒,對付這樣一個柔弱的女人居然還使出這麼殘酷的辦法。萍真後悔剛才為甚麼要逃跑,以至遭來更加嚴厲的束縛。
“嗚……嗚,嗚……”萍實在是忍受不了了,她此時寧願去死,也不想再受這樣的折磨。“大哥,這妞好象要說話”“別理她,趕路”刀疤沒有理會萍的示意。“嗚……嗚”萍一邊呻吟,一邊死命地掙扎。“他媽的,這妞真他媽不安分。把她嘴�的毛巾拿出來,看這婊子想幹甚麼?”刀疤終於讓萍搞的有些沒耐心了。
“哇……哦”毛巾剛一拔出來,萍就忍不住要嘔吐。“幾位大哥,我求求你們了,我不跑了,你們把我腳上的鐵鏈拿掉吧,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也不叫,別再用毛巾堵我的嘴了,我氣都快喘不上來了。”萍用近乎哭的腔調哀求刀疤一夥。
“閨女,實話告訴你,這腳鐐的鑰匙我們也沒有,要到了買家那�才能打開,你就將就將就吧,誰叫你不老實呢,至於嘴嘛,等天亮進了山�再說,堵上。”
還沒等萍做出回應,毛巾又重被塞進了嘴�,外面又纏上幾圈膠條。萍拼命扭動繩索捆綁下凹凸豐腴的身體並嗚嗚地叫著以表示強烈的抗議。“他媽的,你還真夠倔啊,不給你緊緊皮,你是不長記性啊,來,把她給我吊起來。”刀疤惡狠狠地說到。
幾個人三下兩下把萍拽到小路邊一棵大樹下,刀疤掏出麻繩,一頭繞過碗口粗的樹枝,另一頭系在萍後背麻繩的交叉處並打好了結。萍感到後背一緊,一股向上的力量將自己拽了起來,由於身體的重量,身上的麻繩深深地勒進了肉�,越來越緊,她感覺快要透不過氣來,身體在一點一點地上升,萍用腳尖努力地夠向地面,但結果是離地面越來越遠。萍整個人被懸空吊在了半空中,腦袋無力地垂在胸前,一頭秀髮披散在臉側,兩隻嫩足在空中做著無用地掙扎,體重加上腳鐐的重量,萍的表情痛苦萬分。
刀疤拿著皮帶,站在萍的下麵,幸災樂禍地觸摸著勒在萍身上的繩索,突然一揮手中的皮帶,重重地抽在了萍的身上,“嗚……阿。”萍擡起頭大聲呻吟著,皮帶開始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萍的大腿、屁股、乳房這些女人最敏感的部位,萍的額頭滲滿了豆大的汗珠子,嘴中的呻吟聲也逐漸變成了來自鼻子的哼哼聲。由於疼痛,萍失禁了,尿液順著大腿滴到了地上,腳下的黃土被滲失了一大片。
刀疤他們打了半天也打累了,坐在地上抽起了煙。“大哥,這�離山口不遠了,進了山,誰也別想找到我們了,等到了石老二家,你還不好好疼疼這妞?哈哈哈哈。”“呵呵,等大哥我爽完了,你們哥倆也有份。”刀疤對同伴說到。原來,石老二是他們的同夥,就住在這深山�,是他們販賣女人的中轉站,通常他們把綁來的女人先帶到石老二的家�,在這�等待買主的到來和進行交易,買主再把買來的女人從這�運走。人販子在販賣婦女時,都會將女人糟蹋一番,一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獸欲,二來是為了徹底摧毀女人的心理防線,任由自己擺佈。
萍被抽打得暈死了過去,涼颼颼的夜風將她吹醒,麻繩捆吊的疼痛使她不自覺地哼哼著,胸前的襯衣扣已不知甚麼時候被解開了,一對白皙豐滿的奶子在繩索地包圍下鼓鼓地向上翹著,上面依稀可見抽打過的鞭痕。刀疤見她醒了過來,掐滅手中的煙頭,讓兩個同伴把她放了下來,繼續朝著黑夜走去。
天空泛起了魚肚白,萍已經被押送了一個晚上,腳碗撕裂般的疼痛也已被麻木所代替,現在已經是在深山�了,除了可以聽到自己走路時鐵鏈與石塊的撞擊聲和人販子不時地私語,就再也聽不到來自外界的其他信號了。在這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山�面,一個人是很難走出去的,人販子把這個地方作為交易的中心,也真是煞費苦心。真不知曾經有多少女人從這�被販賣到別的地方。萍擡頭向山上望去,正好趕上朝陽從山的那邊升起,陽光透過樹林劃出萬道美麗的光線灑在自己的臉上,似希望之火重新點燃,刹那間對自由的嚮往傳遍全身。“我決不能被他們賣掉,我一定要找機會逃跑,就算是爬,我也要爬出去。”萍暗自思量。有了昨天晚上的教訓,萍對這次的逃跑計畫考慮得非常慎重,如果再失敗的話,後果……再者,現在不僅上身手臂被繩索緊緊地捆著,而且還戴著近30斤的腳鐐,並且腳上穿的還是一雙高跟涼鞋,在這樣的地形�行走,是困難且緩慢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先從人販子的視野中消失,然後再尋找出路。可是,這麼長的時間從哪里來呢?要等待機會,耐心地等待。想到這�,萍感到自己仿佛又看到了自由的曙光,身上的疼痛已不知不覺好了許多。
雖然是在山�,但晌午的驕陽依然能把趕路的人曬得汗水淋漓,刀疤的兩個同夥還要一左一右架著一個手腳被束縛的女人,與其說是架著,不如說是擡著,萍在繩索重鐐的關照下怎能像常人一樣走路?這兩個傢夥被累的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大哥,咱們一個晚上都沒有休息,現在安全了,也該找個落腳的地方好好歇歇了,等下午涼快點再趕路吧。”一個傢夥終於忍不住了。刀疤擡頭看了看炎炎烈日,對同伴說:“轉過前面有個瀑布,下面有水塘和平坦的石頭,那�可以落腳。”
果然沒走多遠,就聽見了水流從高處傾瀉飛濺的聲音,一條瀑布出現在面前,下面聚成一汪清澈見底水塘。一見到水,幾個人都興奮得恨不得馬上跳進去涼快涼快。萍被捆在水塘邊的樹上,看著刀疤他們毫無掩飾一絲不掛地在水塘�洗澡。“大哥,給那妞也洗洗吧。”“好啊,我還沒給女人洗過澡呢,哈哈哈。”說罷,幾個人躥上岸,把萍帶到水塘邊,用刀子割掉了她的衣服。一個全身赤裸,被麻繩和鐐銬捆綁著的美女呈現在了眼前,萍赤身裸體地站在三個男人面前,任由他們淫穢的目光上下打量,羞辱得無地自容。刀疤一把將她抱了起來,走進了水塘,手在她的乳房、蜜穴�不停地搓揉。“嗚……恩”萍呻吟了起來,不知不覺下身竟流出了蜜水。麻繩因為受水的浸泡,一下子收緊了不少,萍一點都掙扎不得。刀疤就勢把陽具插進了萍的私處,在水中大力地抽插了起來,岸上的傢夥看著他抱著那女人在水中一起一落地快活了起來,心中早已癢得受不了了,紛紛握住了自己的老二開始自慰。刀疤見了,嘿嘿一笑,把萍放在了岸邊,對著她的臉握著陽具上下搓動,一股粘稠的精液噴射在萍的臉上,那兩個傢夥也不甘示弱,前後也將精液射在萍的嘴上、眼睛上。
折騰夠了,刀疤他們歪歪斜斜躺在石頭上打起了午酣,萍躺在岸邊的石頭上,尋思著怎樣逃跑,眼下的機會難得,刀疤他們走了一夜,一個個累得筋疲力盡,趁他們現在剛睡著,此時不跑,更待何時。想到這�,萍悄悄挪動了一下身體以做試探,“嘩啦,”一聲鐐銬碰撞地面的聲響嚇了萍一大跳,不過那幾個人好象絲毫沒有察覺,可能是瀑布飛濺的水聲幫她掩飾了不少動靜的緣故。
萍的膽子大了起來,她開始嘗試從地上坐起來,首先她必須趴在地上,然後讓膝蓋和頭著力,使自己能跪起來,這期間還要儘量保持不讓腳鐐發出太大的聲響。經過幾次努力,她成功的跪了起來,剩下的就是站起來悄悄地走出去了,萍幾乎不敢呼吸了,她慢慢地站了起來,一點一點向外面挪動著腳,“噹啷”腳鐐響亮地碰到了一塊突出的岩石,萍感覺心快從嗓子眼�跳了出來,呆呆地立在了那�。
刀疤他們睡得很死,沒有被響聲吵醒,也許他們認為在這樣的地方,一個被束縛著的女子是無法逃出去的吧。萍站了半晌,確信他們沒有察覺後,一點一點地向樹林挪去,終於,她慢慢遠離了他們的視野,可以大膽地向前走去。
腳鐐死沈死沈,腳腕疼得難以忍受,萍一瘸一拐地拼命向前走著,能夠得到這樣的機會,再大的痛苦又算得了甚麼。由於緊張,萍感到腳下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緊接著整個人向前撲了過去,摔在了地上,原來是一段枯枝纏住了腳鐐,費了半天勁才把腳鐐從樹枝上弄下來。萍打算把捆住手臂的麻繩和堵在嘴�的毛巾弄出來,她找到一塊岩石,背靠著它開始磨繩子,可是剛剛被泡過水的繩子又緊又滑,磨了半天也沒見效果。手腕被勒出了血道,疼得鑽心。萍心急如焚,這樣下去,還沒跑多遠就會被發現追上,那可就真的完了。正在這時,遠處傳來了簌簌地腳步聲,萍驚得差點暈了過去,刀疤他們已經追上來了。
還未來得及仔細想,萍就已經看見不遠處樹林中人頭攢動地向這個方向跑來。“他們來的可真快”萍心想。眼下跑是不可能了,藏?又沒有能夠完全隱蔽的地方可以藏身。也管不了這麼多了,萍就勢滾到了草叢中,全身趴在了地上,大氣也不敢喘一喘。剛剛藏好,刀疤他們就從眼前跑了過去。好懸!差一點就要被抓住了,萍暗自慶倖。
可腳步聲過去沒多遠就停了下來,萍剛剛鬆弛下來的神經又一下子緊繃了起來,難道他們發現我了?透過草叢,萍看到那幾個人在低頭看著甚麼………。。
刀疤果然是個狡猾的人販子,他順著萍在地上留下的腳印一路追來,到了這�,腳印沒有了,這說明她就在附近。因為萍穿的是高跟鞋,在這樣鬆軟的土地上留下的痕跡很容易辨認。萍絕望地閉緊了眼睛,此時的命運只有由上天來安排了。刀疤他們也很快就發現了草叢背後捆綁在那�的萍。“哈哈哈哈!老天真是他媽的心疼咱們兄弟,沒有讓到手的肥鵝飛掉,兄弟們!把這個賤貨給我拖出來!”二個男人過去一左一右把萍從草叢�架到了刀疤面前,“啪、啪……”刀疤用力抽打著萍的臉龐,“你個臭婊子,我叫你跑!”刀疤一邊罵一邊不停手地抽打著萍。
“這婊子真他媽的夠野啊,五花大綁戴著腳鐐還不塌實”一個同伴說道。萍倔強地擡起頭,怒視著眼前的人販子,雖然嘴�發不出聲音,但是她還是嗚嗚地表示著自己的不屈服和抗議。刀疤此時心中感到眼前的這個女人可不象以往那些畏懼暴力、無比順從的被賣女,她有思想,還有膽量。如果不嚴加看管,早晚必受其害。想到這�,刀疤停止了抽打,讓二個同伴帶著她繼續趕路,為防意外,刀疤讓同伴把萍駟馬攢蹄捆好,找了個粗木棍,從萍背後和腳上的繩子穿過去,然後擡著她走。萍整個身體反弓著被吊在一根木棍上,痛苦異常,兩隻肩胛骨向後向上高高撅起,手腕和腳碗撕裂般火辣辣的疼。由於身體反弓加上嘴�還塞著毛巾,萍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窒息,喘不過氣來,走了沒多遠,豆大的汗珠子順著雙頰滴答滴答留到了地上。更可氣的是後面那個擡她的傢夥手還不老實,時不時地撫摩幾下她光滑的大腿和嫩足。山路崎嶇,萍的身體在空中上下顛簸、左搖右擺,每一次搖擺都會帶來巨大的痛苦,萍忽然感到下面一熱,一股熱流穿透了絲襪順著大腿根流了出來,小便失禁了。這可把後面那個傢夥樂壞了“快看呀!這騷娘們尿了!流了一地,哈哈!”“應該在她的逼上上把鎖,省得她亂撒尿”前面的傢夥說。萍想到自己被人像擡畜生一樣的吊在棍子上,還遭到了如此嘲笑,屈辱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順著雙頰留了下來,落在了路邊的花瓣上。
正在走時,刀疤突然停下了腳步。“怎麼不走了?大哥?”“前面好象有人。”“不會啊,這深山老林�,怎麼會有人來呢?”“看那……”順著刀疤指的方向,對面果然有兩個人向這�走來,他們好象也注意到了這邊,站在那�眺望。
“怎麼辦?大哥,要不要躲一躲?”刀疤眯了一下小眼,沈思一下說:“不,躲反而會被懷疑,迎過去!”“可是這……”“一會我來應付”說罷,幾個人加快了步伐,朝對面的人走去。不一會,兩撥人就相遇了,刀疤上下掂量著對方,從裝束上看,像是進山打獵的。“兩位是來搞山貨的?”刀疤笑咪咪地說。“是啊,這季節正是好時候,山貨比較多,幾位是?呦!這姑娘是??”“咳!別提了,她是我親妹子,逃婚!剛被我們抓到,不願跟我們回去,尋死覓活的,不這樣綁著制不住她,爹媽在家都快急瘋了!”刀疤回道。“哎!這姑娘也夠可憐的,”“沒法子啊,山�人嫁閨女的聘禮能養活一家人,如今人家的聘禮收了,人跑了咋交代啊。”“哎!你們也不容易啊,行了,你們還是趕緊趕路吧。”萍聽到這些,拼命地掙扎著,嗚嗚地呻吟著,希望眼前這兩個獵人能識破人販子的詭計救自己出去,可一切都是徒勞,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希望從面前漸漸消失,而毫無為力。
將近傍晚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密林深處的一間老房子前,刀疤止住同伴,隻身一人進了屋,半袋煙的工夫,同兩個人一起走了出來,一人是一位老者,相貌醜陋,微有駝背、鑲一嘴金牙,另一男子滿臉橫肉,身材高大魁梧。刀疤很尊敬這位老者,據說此人原先是山�的鬍子,姓袁,人稱袁金牙,生性殘忍狡詐,曾經稱霸一方,打一手好槍,當年剿匪時,死在他槍下的解放軍官兵就有不少,其中還不乏歷經了幾次大戰役的戰鬥英雄。這之後被政府通緝多年在逃,無處藏身,只好躲進了這深山老林,幹起了販賣婦女的勾當,旁邊的大個子是他當年和城�一個很有名氣的窯姐所生,從他滿臉的橫肉和陰險的目光可以看出此人的兇殘也絕不在其父之下。因為這�地形複雜,人跡罕見,所以多年以來,父子倆的人口生意越做越好,慢慢竟變成了中國向境外輸出妓女和性奴隸的主要來源地。綁來這�的姑娘,大部分被轉賣到俄羅斯海參威的妓院充當妓女,也有東歐一些地方的妓院老闆來這�挑選上好的貨色,然後這些女人要被輾轉幾個國家長途販賣,最遠的曾經被賣到了巴拿馬的妓院或者是衣索比亞的性奴隸市場,經過這麼多人倒手,最後的價格也是不菲的。
袁金牙看著吊在木棍上早已筋疲力盡的萍,對刀疤說:“這妞你想賣多少錢?”“哦!呵呵!價錢好說,價錢好說,就是不知您老看得上不?”“你小子少他媽來這套,3000塊,你把人放這,否則就走人。”“老太爺!您高擡貴手,我們哥幾個這一路不容易啊,中間還差點讓這婊子給跑了!這妞盤子亮,我們收她的價也不止您這些個呀。”“4000塊,一口價,我他媽做一次好人,多那1000你們兄弟去喝酒吧。再給我還價,我可要翻臉啦!”刀疤聽罷連忙點頭答應,4000塊成交了。袁金牙心中竊喜,其實他明白:就眼前這塊肥嫩的肉,能好好敲上毛子一筆,所得的價錢又何止4000?
萍迷迷糊糊覺得被人從木棍上放了下來,身上的繩子和腳鐐也被解開了,2只胳膊像折了一樣無力地垂在兩側,已經不聽使喚了,這可是她2 天一夜以來第一次被鬆開束縛感受手腳的自由。但是馬上大個子走了過來,手�提著一副厚重的鐐銬,鐐銬很奇特,首先是套在脖子上的金屬圈,在卡嚓一聲鎖死後一條鐵鏈連著一副大約15毫米厚的手銬將萍的雙手鎖死,手銬下面的鐵鏈連著腳鐐,腳鐐也很厚重,兩腳間的鐵鏈粗厚沈重,但不長,有30釐米左右。大個子一邊給萍鎖上鐐銬,一邊對身邊的刀疤說這副鐐銬是在俄羅斯定做的,材料經過了特殊的處理,鋼挫和電鋸打磨根本就無法打開這種鐐銬,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鑰匙,另外還有一種時間限定的功能,通過脖子上的項圈設定鐐銬自動打開的時間,在這以前,即便用鑰匙,也無法打開鐐銬。一般他們在給被賣女鎖上這種鐐銬時都採用時間設定的方式,這樣比較安全。時間可長可短,最長可設定五年。說罷,他將萍的時間設定到一年,鎖死了開關。
萍無力地擡起手,撫弄了一下淩亂的發際,鐐銬發出清脆的金屬撞擊聲,隨即,大個子推搡著她向屋�走去,而袁金牙和刀疤在一邊忙著點錢算帳。進了屋子,發現�面很大,正堂兩邊各有間房,轉過正堂後面還有一間,像是儲藏室,大個子挪開屋子內的一個櫃子,在牆上扳動了一下,忽然只見牆上打開了一扇石門,原來這�面還有密室!萍被大個子推進石門,進石門後是向下的臺階,然後拐彎進入走廊,走廊盡頭一扇厚鐵門緊緊鎖著,�面泛著微弱的燈光。打開鐵門後是一個大房間,房間被鐵柵欄分成了四五個囚室,中間是過道,大個子打開其中一個囚室,把萍推了進去,返身鎖上門,走了。隨著門鎖卡嚓卡嚓的落響,一切又恢復了寂靜。萍恐懼地蜷縮在牢籠的一角,心中的噩夢在不斷延續……
四周一片寂靜,除了萍偶爾動動身子,鐐銬發出的金屬撞擊聲,就再也沒有任何聲音了。萍的思緒在寂靜中飄得很遠,她想起了在家的時光,想起了孩子、母親甚至是前夫。比起現在的處境,那些過去看似的不幸仿佛也變的充滿了人情。萍開始後悔自己的倔強和衝動,如果換做一個溫順的女人,也許現在還在過著雖有煩惱但還平靜的清淡生活。那也要比成為別人的一件物品,任由發落強得多。現在這個樣子,生還不如死。想到這�,萍留下了絕望的眼淚。
販賣(二)
經歷了一路的痛楚折磨,萍不知不覺地沈沈睡去,直到鐵門發出沈重的撞擊 聲將她驚醒。進來的是大個子,從他臉上不懷好意的壞笑,萍很快意識到下面將要發生什麼。她出於本能地縮緊了身體,向後面靠去,臉上的表情驚恐無助。
大個子也沒有多餘的廢話,很利索地把萍身上的衣服撕了個精光,只剩下一個裸露著豐腴侗體、戴著手銬腳鐐的女人躺在地上。大個子一把抓住萍的頭髮,將她拽起來跪在地上,她那柔軟的嘴唇正好對著褲子�漲大的陽具。陽具深深地插進萍 的喉�,在那�放肆地四處遊動,令萍感到陣陣的噁心,大個子有些不高興,抓住萍頭髮的手猛然向後下拽了下去,萍的頭一下子被動地向後仰去,目視著陽具從上面深深地插了下來……正在大個子對萍進行蹂躪的時候,鐵門的一側站著一個人,袁金牙。他無意中看到了眼前的這一幕,又默不做聲靜悄悄的走開了。
深夜,袁金牙將睡夢中的萍叫醒,親自把一副2MM 厚生鐵打制的貞K 帶鎖在了她的身上,他是不希望眼前這個女人在交易前發生什麼麻煩的事情。
許多個日日夜夜,萍就在這昏暗潮濕的地下牢籠中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就像一隻被人圈養牲畜,饑餓和寒冷侵襲著全身上下,見到主人手�的硬饅頭和稀飯像看到了一桌子的美味佳餚,拖著鐐銬的身體緊緊貼在冰冷的鐵柵欄門上用乞求渴望的眼神望著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什麼尊嚴、廉恥、女人的矜持、羞澀通通已不復存在了,暴露出了作為人最簡單的需求。萍為了儘快獲得食物有時會被要求擺弄一些淫蕩、猥褻的肢體姿勢和舞蹈,時間久了居然也能像夜總會的裸舞女郎那樣搞出各式各樣勾人魂魄的姿勢了,袁金牙真是老到,他已把當初那個倔強、桀驁的女人訓練的服服貼貼、百依百順了。除此,萍每隔一段時間會被注射一種藥物,據說,這種藥物可以長久保持女人膚質具有彈性和光澤,同時可以有效改善體形,它�面的藥物成分會使乳房發育的很豐滿,腰間的脂肪向下移動,臀部的脂肪會進一步變厚,達到豐乳肥臀。泰國和東歐的妓院經常為妓女注射這種藥物以保持她們迷人的身材和漂亮的臉蛋。
一天夜�,萍恍惚中聽到一陣碰撞聲,一個年輕女子被大個子連推帶搡押了進來,女人上身被麻繩緊緊地綁著,腳上帶著一副黑漆漆的腳鐐,嘴上一條布帶纏在腦後,�面鼓鼓囊囊,像是塞滿了東西。那女人似乎很倔強,不停地在掙扎和反抗,大個子打開萍對面的牢房,把她拖進去剛要轉身縮門,女人從後面向他撞來,險些將他撞倒。大個子一下被激怒了,他怒不可泄地抓住那女人的頭髮,把她拽到屋子中間,掏出一條繩子系在她後背,再穿過屋頂的鐵環,用力把她吊了起來,然後罵罵咧咧地走了。萍這時才來得及仔細打量眼前的這個女人,她看上去很年輕,身材勻稱,凹凸有致,一頭長髮披散在臉前,遮住了垂在胸前的面部,及腳腕的連衣長裙使人顯得修長,裙子上很多地方都已經襤褸破損,可見一路上也是受盡磨難,一雙白色細帶高跟涼鞋包裹著一雙白嫩修長的玉足,腳趾上左右交叉著兩條細細的帶子,拇指在鞋尖向上微翹著,其他腳趾依次向後排列,指甲上塗著黑紫的指甲油。女人被吊的很痛苦,每扭動一下,身體都會在空中旋轉半圈,那副腳鐐看上去也不輕,女人的腳動也不敢動一下。萍幾乎是一晚沒有睡著,對面女人嘴�嗚嗚的呻吟聲讓她揪心。天剛亮,大個子就來到牢房,把那個女人從鐵環上放了下來,女人一灘軟泥似的倒在地上,大個子解開她身上的麻繩,換成了和萍身上一樣的鐐銬。
萍慢慢知道了那個女人叫曼,是個在校大學生,返校途中被人販子拐騙賣到了這�。曼是個清秀的女孩子,典型的江南美人,剛來的幾天�終日以淚洗面,不吃不喝,沒多久也就平靜了下來,現在不時的和萍聊一聊自己的身世和經歷,形同姐妹。
由於藥物的作用,萍和曼的奶子發育的越來越豐碩,現在每天都要從�面擠出許多奶水,否則漲痛得使人受不了,擠出的奶水都被大個子收走了,如果數量不夠就會被罰挨餓,所以除了吃飯聊天,姐妹兩人大多數時間都在用戴著手銬的雙手努力地擠奶以求達到數量。
這一天,牢房的鐵門打開後,進來的是袁金牙,在他身後還跟著一個身材高大一臉鬍鬚的洋人。萍和曼感覺到今天的氛圍不對,姐妹倆相互對視了一下,怔怔地望著來人。“強森先生,請您仔細過目,我對您的承諾是絕對不會有偏差地,哈哈哈“袁金牙疵牙咧嘴地對那個毛子說。”恩,我喜歡的類型,2 個我都要了哈哈哈哈,袁老闆,你出個價錢吧。“毛子說。”好!既然強森先生這麼識貨色,我袁金牙交你這個朋友,30000 元!怎麼樣?“”NO NO NO,袁老闆,你在和我開玩笑,這樣的貨色你幾千塊就可以買到了。“”強森先生,話不能這樣講啊,我買了她們,還要養活她們啊,在她們身上花的錢難道讓我白花啊“”這樣吧,20000 塊,我們成交OK?“”不行,最少也不能低於24000 元,否則我去找其他買主“袁金牙假裝沒有耐心了。”好吧,袁老闆果然是會做生意,哈哈,我們成交,明天我的人過來發貨。“”呵呵,痛快!今晚我請強森先生嘗嘗我們山�的野味,請!“
萍和曼目瞪口呆地聽完兩人的商品買賣交易,而交易的商品就是自己的肉體,她們不知到明天自己將會被作為商品運到什麼樣的地方去,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屋子�一片寂靜,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過了許久,鐵門被打開了,大個子提著一個大皮包走了進來,他先打開萍的牢門,沖著萍嘿嘿的笑了兩聲,說“還真捨不得你呢,心肝。”說完他從包�拿出一個類似於噴槍的東西,只不過前部是幾排密密麻麻的針尖組成的圓圈內有個倒A 字的圖案,原來這是一個專門為妓女或性奴隸打上標識的紋身機,針頭組成的圖案區分著奴隸所從屬的主人。隨著萍的幾聲慘叫,大個子在她的乳房、臀部打上了印記,並熟練地為她上了一次性鋼制乳環、臍環和陰環。曼也被同樣的裝扮了一番。
販賣(三)
大個子做完這一切,很滿意地走了出去,剩下兩個被標上標籤等待出售的女人。被刺過記號的地方火辣辣得疼,穿了環的皮膚立刻腫脹了起來,萍用帶著手銬的手輕輕地撫摩著痛處,試著想把鋼環取下,但鋼環合上後卻沒有一絲縫隙,就像是整體鑄造的一樣。曼則在一旁不停地抽泣,片刻後,她對著萍說:“萍姐,我不想被他們賣到國外,我們該怎麼辦?你快想想辦法啊。“萍看著眼睛哭得略微紅腫的曼,嘴角閃出一絲無奈的微笑,她何嘗又希望自己被人賣到遙遠的異國他鄉,遠離甚至永遠的與親人分別呢,可是,自從被販賣的那一天起,自己就從沒放棄過逃走的念頭,一次次的逃走,一次次地被抓回來,身體自由受到嚴厲的限制,手銬、腳鐐、鐵牢、身上的標記……在這深山老林�,就算跑又能跑多遠?跑到哪里去?自己早已認命了,可是曼還很年輕,她有理想、有前途、這樣被毀了的確令人感到惋惜,每當看到她那雙水汪汪、略帶天真的大眼睛,萍都會覺得心疼。作為大姐姐,自己還沒有為這個小妹妹做過什麼,哪怕是為她挽挽發際,萍心�在想:如果將來有機會,一定會盡力幫助她。
這個晚上,姐妹兩人誰都沒有睡好,寂靜的夜晚,牢房�輾轉發出的金屬鐐銬與地面的撞擊聲格外刺耳。天亮的時候,強森的人在大個子的帶領下,打開牢門走了進來,這是一群訓練有素的打手,個個高大彪悍,兇殘的眼神令人望而生畏。幾個人進來後不由分說,分別把萍和曼從牢房�拖了出來,在那麼多男人面前,兩個赤身裸體,鐐銬加身的女人既驚恐又羞澀,她們很快被人架著來到了地面的空場,萍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外面的空氣和陽光了,她閉著眼睛努力地呼吸著
……外面的溫度很冷,好象已經是隆冬了,萍想著自己被關進去的時候還是初秋,算來也應該有好幾個月了,這幾個月,不但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身體也從原來的柔美、勻稱變成了現在的豐腴,一對碩大的奶子在胸前晃來晃去,上下起伏,乳頭上的鋼環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細腰下肥碩的臀讓人看了就想去淩虐。曼也從剛來時的苗條修長變得越發豐滿結實,兩隻奶高高地聳立在胸前,紅潤的乳頭上還掛著未幹的奶水。屋外的空地上,袁金牙正在遠處和強森私語,大個子陪著4 個打手一左一右的架著萍和曼,不遠處樹林栓著7 、8 匹馬,有2 個人正
在從馬身上往下搬東西。他們搬的是厚重的木箱子,這箱子長1 米寬60高1米,箱子�面實際上是鋼條焊成的籠子,人放進去只能保持坐著或者跪著的姿勢,在箱子的一側,有個10CM見方的洞,是通風用的。
袁金牙用密碼打開了姐妹兩人身上的鐐銬,但馬上就被打手們用牛筋緊緊地反捆了起來,兩隻手被高高的吊在背後,並另外加了一副手銬。手銬上接一條繩直接從肩膀繞到前面分別系在2 個乳頭上的鋼環�。牛筋的特點是被捆的人越掙扎就會感到越緊,尤其是碰到水就會緊縮。姐妹兩人本來就豐滿的身體讓牛筋這麼一勒,更加凹凸有致,呼之欲出了,腳上的腳鐐被換成了30斤重鐐,而且是用母釘釘死了的,釘的時候把兩個女人疼得眼淚花花直流,3 個大漢一個掄錘,兩個摁著費了半天勁才算把腳鐐釘好。接著還要被戴上口鎖,口鎖是鋼制環形的,可以圍繞頭部嵌在嘴上,在腦後鎖死,嘴部有硬質橡膠口球,隨著口鎖的鎖死,口球會全部進入口出,打開氣閥,口球開始在嘴�充氣,以達到把嘴全部塞滿不留一絲空隙,使帶口鎖的人不能發出聲響。最後,萍和曼分別被人擡進了箱子,腳鐐被用鎖固定在箱子�的鋼柵欄上,當箱子蓋蓋上鎖死後,透過側面的通風洞,鋼柵欄後面一雙無助絕望的眼睛在流淚,她們開始踏上了通往性奴生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