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友站 番號最齊 新作上架最快!(每天更新百部AV)
請使用轉址到網站新介面模板瀏覽, 10 秒后,
会转跳到 ==> https://18av.mm-cg.com
小說名稱:[人妻熟女]海鷗與櫻桃 (1-4+番外)
文字放大: 自訂文字大小: 行距:|
第一章;初入豪門(上) 下午兩點四十五分,中華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機平穩地降落在虹橋。 陰雲密布的天空籠罩著一片空曠,晦暗得像是張生悶氣的臉。 沿海的南方城市,冬天居然也出奇的冷。艙口的冷空氣猛地灌進來,父子倆 打了個寒顫,各自裹緊了衣服,小心地下了舷梯。 臘月二十五了,再過幾天就是新年。魚貫而出的乘客,都趕著回家團圓,形 色匆忙。 譚海松卻刻意把每一腳都邁的很踏實,猶如閑庭信步般,悠然自得。 「恁冷!」譚海松對于兒子,幾乎沒有任何了解,現在只剩兩人相依爲命, 總是相對無言,難免會覺得愧疚和尴尬,「帽子也不戴,看你耳朵凍嘞!」 亞鷗一路都面無表情的沈默著,兩片嘴唇像是挂了把生鏽的鐵鎖。 父親的普通話夾雜著濃重的口音,就像城鄉結合部的野雞一般不倫不類。可 飛機上偏還跟隔壁座位的一對兒摩登女郎聊得熱火朝天。幫人家端咖啡、拿雜志, 忙的不亦樂乎,最後竟然交換了電話號碼並合影留念,說是有緣再會! 「五十多歲的老大叔了,還跟色中餓鬼似的……」周圍乘客竊笑不已,暗罵 他,「癞蛤蟆想吃天鵝肉!」 真是丟人到九霄雲外去了!亞鷗惱得恨不能直接跳飛機,就更懶得待理父親 了。 「估摸著要下嘞!」兒子沒搭腔,海松裝作若有所思地道,「上海算是南方, 下不了雪吧?」 「嗯。」亞鷗鼻孔裏哼出了一股白濁的氣息。 「要是雨,就麻煩嘞!」海松繼續厚著老臉沒話找話,忽然靈光閃現,道: 「還好你姑媽安排了你表姐來接咱們。」 果然,亞鷗眼睛裏掠過一絲亮光:「表姐?」 「嗯…」海松故意拉著尾音,顯得意味深長。 雖然素未謀面,然而常青藤名校的表姐,對于小縣城出身的少年,尤其還是 個成績優異的好學生,幾乎就是頂禮膜拜的偶像。 「就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那個?」亞鷗克制著激動的心情,道。 「嗯,你表姐從美國紐約回來過春節啦。」 海松特別強調了「美國紐約」,可不是隨便什麽街邊的「紐約理發店」之類, 而是貨真價實的「美國紐約」! 電視新聞裏也經常聽到紐約,聯合國啊、恐怖襲擊呀、華爾街啦,遙遠而陌 生,簡直就像另一個世界。如今,卻像走在前面的那兩個時髦女郎的細腰豐臀, 水蛇似的搖擺著,仿佛觸手可及。 譚海松環顧四周,心情頗有些豪邁:「等你讀完高中,也送你去美國!」 亞鷗顯然缺乏父親的熱情,只隨口敷衍道:「到時候再說吧!」 譚海松皺了下眉,就像好容易點著的柴火被兜頭淋了盆冷水。 春運時節的機場大廳裏比肩接踵,呼喊叫嚷聲此起彼伏。 亞鷗拖著兩個沈重的行李箱,跟在正打電話的海松後面,艱難地擠到了門口。 「餵,靜鷗!我是你舅舅啊!嗯,我們到了,剛出來!你在哪兒嘞?哦,知 道了!嗯,好的,行!」 譚海松「啪」地合起那部老舊的夏普翻蓋手機,滿臉喜色道:「你表姐過來 了,咱就在門口等她!」 父子倆把行李箱靠牆立住,認真觀察著來往進出的男女老少。大城市的人, 精神面貌也好得多,每個都容光煥發,衣著亮麗。其中還混雜著高頭大馬的外國 人,更不乏金發碧眼的美女,即便包裹的嚴實,依然前凸後翹,異常惹火。 海松眯著眼點了根香煙,「外國的女人就是白啊!」 亞鷗聯想到生物課本裏的圖片,撇嘴道,「跟血友病一樣!」 譚海松幽然吐出個煙圈,正要反駁,手機忽然響了。 「餵,靜鷗啊?嗯,是在門口,就我跟亞鷗!對,兩個大行李箱。你到了? 在哪兒呢- 哦,看見你了- 靜鷗,這邊兒!「 一位時尚靓麗的窈窕女子沿著園圃間的鵝卵石小路迤逦而來,宛如暗夜中由 遠及近的燈塔般,越來越閃亮。她身材高挑,約有一米七五左右,兩條細直的長 腿,宛如模特一般。 脖子裏系著條印花的絲巾,穿著件卡其色大翻領的風衣,裁剪得極爲合體, 斜束著腰帶,衣擺迎風鼓動,更帶著些許優雅的隨性。純白色緊身褲裹束著她纖 長的美腿,搭配著一雙工藝精美的黑色尖嘴兒的方跟小皮鞋,俨然一派文藝範兒。 女子走近前來,微笑著伸出了手,「舅舅,你好!」 她眉清目秀,精致的鵝蛋形臉龐略施粉黛,就像藝術大師嘔心瀝血的作品, 蘊斂著珍珠般的光彩,照得人心裏甚是通透。 「你好,你好!」譚海松上下打量她,眉開眼笑地道,「嗯,像你母親,真 是個齊整閨女!」 「呵呵,謝謝您!」女子臉頰飛起兩團紅暈,煞是嬌俏動人,「我媽陪外公 參加酒店的年會去了,所以派我來接您跟亞鷗,希望您別見怪!」 「不會,不會!」海松忙不疊地道,轉身又催促兒子:「亞鷗,快叫表姐啊!」 她就是姑媽家的表姐嗎?二十三四歲年紀,身姿苗條,烏黑柔順的秀發绾成 個看似簡單卻造型優美的發髻,宛若堆疊的雲,尤其兩條象牙筷兒似的颀長秀腿, 簡直像電視裏跳熱舞的韓國美女天團。常春藤的氣質就是與衆不同啊! 「表…表姐!」少年有些自慚形穢,嗓子也不合時宜地卡殼了。 「呵呵,亞鷗你好!」她親昵地拉住表弟的手,一陣淡雅的茉莉香氣令人欲 醉,「我叫梁靜鷗,也是『海鷗』的『鷗』,跟你一樣呢!」 她的話消除了許多陌生感,攏鬓角的輕盈動作,更讓亞鷗癡然想起許絡薇, 「嗯,靜鷗表姐好!」 「你姑媽經常挂念你呢,誇你懂事,功課又好!」梁靜鷗聲音清脆如珠落玉 盤,格外悅耳動聽。 「也不是啦…」少年有些忸怩,抻著舌頭講普通話,卻覺得鹦鹉學舌般古怪。 「呵呵,還挺謙虛的嘛!」 梁靜鷗拍著亞鷗的肩膀,露出一排整齊的雪白牙齒,羽扇般細密的睫毛掩映 著明亮透澈的雙眸,仿佛叢林中的湛藍湖泊于陽光下閃耀著甯靜深邃的光芒。 旁邊不知何時冒出來個中年男人,西裝墨鏡,鐵塔般伫立著。 「這位是…」海松疑惑地轉向靜鷗。 「啊,不好意思!」靜鷗雙手合十,抱歉道,「嚴大哥,你就自我介紹下吧!」 「譚先生您好,我叫嚴石,嚴格的嚴,石頭的石。我是您的專職司機,請您 多關照!」西裝男摘掉墨鏡,露出張棱角分明的國字臉,恭敬地鞠了個躬。 「嚇我一跳,還以爲幹啥的呢…」譚海松朝嚴石遞了根煙,順口又調侃道, 「車還沒買呢,先聘了司機,哈哈哈!」 「嚴大哥把車開來了。」梁靜鷗柳葉眉彎成了月牙兒,绛唇巧笑,麗色生春。 她樹葉般輕飄的一句話,卻讓亞鷗思緒紛飛。表姐家境殷實,從姑媽之前去 融城的排場就可以窺見端倪。初次見面就能送輛車,頂多幾十萬塊錢也就算了。 擱融城是筆巨款,對于大城市的人或許無足輕重。但爲什麽還要配司機? 「唷,那敢情好!」譚海松是喜歡車的,興奮地道,「走,咱瞧去!」 行李箱交給了嚴石,亞鷗兩只手斜插在羽絨服的衣袋裏,緊跟在表姐和父親 的身後。沿途經過各種品牌和款式的轎車,都忍不住猜測。 會是這輛銳志?還是那台雅閣?或者是部君威?再則,姑媽之前去融城乘坐 的清一色奧迪A8,應該對質量可靠的德國貨情有獨衷吧。那樣的話,莫非是A6? 嗯,低調穩重,適合事業有成的商務人士。亞鷗成竹在胸地推想著,深爲自 己的邏輯能力所折服。但是,老爸那種性格,恐未必會喜歡A6吧? 梁靜鷗卻引著海松轉進停車場所謂的VIP 區域,裏面幾乎全是寶馬和奔馳之 類,更不乏法拉利和保時捷等造型酷炫的跑車。 亞鷗頓覺震驚不已,難道是貴得離譜的奔馳或者寶馬?要是駕著輛奔馳或者 寶馬駛過融城塵土飛揚的街道,多半將引得路人駐足行注目禮,未免太張狂了點 - 咦,那台是什麽車? 靜鷗和海松也幾乎同時停住了腳步。 一部與衆不同的黑色轎車安靜地泊在角落裏,就像暗夜裏流光溢彩的王冠, 尊貴奢華,富麗典雅,磁石般吸引著亞鷗的眼睛。 「不會是它吧?!」亞鷗暗吸了口冷氣。 那台車的前燈忽然閃爍,「嗚- 嗚- 」地兩聲低吼,就像馴服的獅子回應主 人的召喚。 身後的嚴石「嘩啦」收起鑰匙串,拎著行李箱徑直走向前去。 亞鷗驚訝地睜圓了眼睛:靠,居然還真是! 「這是啥牌子的?」譚海松弓著腰、背著手,端詳那座展開雙翅的B 字型立 標,興奮溢于言表:「都沒見過啊,看著不賴嘞!」 「賓利的慕尚,特別訂制版。」靜鷗柔聲細氣地道。 風把表姐的話吹進耳朵裏,少年卻猶如被綸音佛語籠罩一般,頭皮都發麻了。 曾經做過一篇關于汽車的英文閱讀理解,裏面提到賓利,具體內容都忘了, 有句話亞鷗卻印象深刻:不但是人選車,車也選人。原以爲姑媽家有錢,就像一 座冰山,照現在看來,他所極力想象的也不過是真正冰山的一角而已。 「值不少錢吧?」海松小心撫摸著閃亮的引擎蓋,感覺比女人的肚皮還光滑。 「也還好,我不很懂車…」梁靜鷗從小錦衣玉食,對于價錢是沒什麽概念的。 她轉向墨鏡男求助道,「嚴大哥或許清楚吧?」 「我只管開車,別的也不了解。」嚴石要給譚海松留個老實可靠的印象,頗 爲巧妙地撒了個謊,又殷勤地爲他拉開副駕駛的門。 該當聾子的時候就當聾子,該當啞巴的時候能當啞巴,海松混迹官場幾十年 了,聽得出他的弦外之意。 「好,好!」他拍了拍嚴石的胳膊,贊不絕口地鑽了進去,車廂內鋪著柔軟 厚實的暗紅色地毯,連車門的喇叭也是暗紅色的網格,「唷,恁寬敞!之前俺單 位那個破桑塔納,跟個蝸牛殼一樣,腿都伸不開嘞! 靜鷗被逗笑了,朝還呆立在旁邊的少年招手道,「亞鷗,快來啊,要回家了!」 高速路兩邊的景物飛快地向後倒退,令人倏然升起禦風而行的快感。 車廂裏的溫度稍微有點高,梁靜鷗已經脫了風衣,解掉絲巾,露出優美白皙 的頸子。米色羊毛衫熨帖著曼妙的身體,僅胸口處有心形的镂空,繡著朵绛紫色 的玫瑰花紋,袒露出一爿冰雪般滑膩的肌膚,仿佛沙漠腹地的水源般彌足珍貴, 平添了許多性感。 「舅舅,要不要喝點什麽?」 「好啊,礦泉水就行!」譚海松應道。 表姐把風衣疊整齊,柔韌的腰肢像小楊樹般挺得筆直,「亞鷗,你呢?」 少年的思緒尚未平複,隨口道:「我喝什麽都行。」 靜鷗打開後中控台的雙層磨砂玻璃門,赫然是個飲料櫃。 接過表姐遞來的杏仁露,亞鷗只是拿在手裏把玩,卻忍不住偷瞄她秀挺飽滿 的乳房,大小和形狀都恰到好處。 「靜鷗,你爸回來了嗎?」譚海松扭過臉來,朝外甥女道。 「嗯,估計會稍微晚些,三點十五分的飛機。」 「咦,你看你!」譚海松埋怨道,「你咋不說呢,咱在這兒等他多好?」 「不是的,國際航班都在浦東。」梁靜鷗道,「他們公司會派人去的。」 「哦- 靜鷗,你九月份結婚了?」 「嗯,沒來得及通知您。」梁靜鷗解釋道,「準備的比較倉促,不好意思。」 哦,她結過婚了?亞鷗一陣莫名的失望,眼神正落在她臀部那一抹渾圓的曲 線。 「也不是,你外公跟我說了,當時你舅媽正病著。」海松的傷感轉瞬即逝, 道,「姑爺回來了嗎?」 「美國的假期才結束,他也挺忙的,所以就只有我回來了。」 「丈夫是美國人?」海松又問道。 「嗯,是的,我研究所的同事。」靜鷗呷了口果汁,道。 她居然嫁給了美國人?亞鷗錯愕不已,腦海裏電光石火間閃過在同學家偷看 過的色情片,美國佬大戰中國妞兒。白種人的家夥聽說都是又粗又長,真不敢想 象溫婉可人的表姐在姐夫胯下宛轉嬌啼的畫面… 郊區公路旁的幾棵細弱的樹苗,正給風扯得東倒西歪,亞鷗努力不去胡思亂 想,開口道:「表姐,你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嗎?」 「嗯,讀的商學院,不過已經畢業了。」梁靜鷗朝表弟笑道。 「你好厲害啊!」亞鷗羨慕道。 「你將來也可以的嘛!」梁靜鷗鼓勵道。 「我英語比較差,恐怕…」亞鷗不敢直視她,低下了頭。 「正好嘛,亞鷗,你該向你表姐多請教!」海松扭過臉來,插話道。 「如果學外語,該去請教子琪姐。她會講英、日、韓三種外語呢!」 「子琪姐是誰?」亞鷗詫異地望著她。 「哦,你還不知道吧?咱們家還有個姐姐,叫趙子琪。」梁靜鷗神秘地朝表 弟眨眼道,「可是個大美女呢!」 亞鷗福至心靈,不可思議地道:「還能比你更漂亮嗎?」 兒子的回答,讓譚海松相當滿意:「哈哈哈,這臭小子!」 「呵呵,挺會說話的嘛!」突然收獲木讷表弟的贊美,而且如此巧妙絕倫, 梁靜鷗頗有些喜出望外,卻道,「等你見到她,就明白了!」 「哎呀,說起來你子琪姐,辦事兒就是體貼周到。晌午的時候還特意打電話, 問我跟亞鷗吃飯有啥忌口沒。」 「今天的晚餐是她安排的,一家人就數她對吃喝玩樂最有研究。」 「哈哈,不光是這嘞,之前跟你舅媽來,也是她接待,那叫個精明能幹啊!」 譚海松稱歎道。 「呵呵,她呀,就是咱們家的王熙鳳。」梁靜鷗笑道,「反正有事兒就找她, 準不會錯。」 譚海松的煙瘾又犯了,伸手到夾克口袋裏的,摸到了煙盒,卻遲疑了一下, 沒掏出來。 「小嚴原來是做什麽的- 叫你小嚴,不介意吧?」 「隨您,沒關系的。」嚴石握著暗紅色真皮包覆的方向盤,身前一堆閃亮的 大小旋鈕和儀表,神情專注而冷靜,就像飛機駕駛員一樣,「我在咱們車隊已經 八年了,之前是爲陳星午總裁服務的。」 咱們車隊,還總裁- 姑媽家到底是做什麽的?亞鷗豎起了耳朵,唯恐遺漏什 麽重要信息。 「陳伯父現在掌管海鷗系,也是外公的老部屬。」梁靜鷗補充道。 亞鷗的胸口噗通亂跳著,強烈的好奇心像是可樂瓶裏翻湧的泡沫:「表姐…」 「嗯?」梁靜鷗抿了下鬓角,「怎麽啦?」 「表姐,你們家,是幹嘛的呀?」 「不是你們家,是咱們家!」梁靜鷗笑著糾正道。 「哈哈哈,亞鷗還啥都不知道嘞。」譚海松道,「靜鷗,你跟他講吧。」 「不是吧…」梁靜鷗睜大了眼睛。 「要不是你爸媽六月份去融城,亞鷗就真以爲自己姓韓呢。」譚海松還是點 了根煙。 「哦…」梁靜鷗沈思片刻,對表弟道,「大豐百貨,你知道嗎?」 「嗯,我們市裏好像就有。」亞鷗想了下,道,「但是我沒進去逛過。」 「爲什麽?」梁靜鷗問道。 亞鷗如實回答道,「裝修得富麗堂皇的,怕進去買不起…」 梁靜鷗莞爾道,「大豐就是咱們家的,而且只是旗下品牌之一。」 「以後再去大豐百貨,是不是喜歡什麽就可以隨便拿了?」亞鷗故意道。 「這小子,淨想好事兒…」譚海松罵道。 「呵呵,也不是啦。」梁靜鷗笑道,「至少要跟經理報你的名字,年底要走 賬的。」 從高架橋下來,駛進新開發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尚是一片寂寥清冷。主幹道 雖然寬闊,車流卻沒有了那股湍急。 「喏,看到那棟樓了嗎- 有『富安置業』字樣的?」梁靜鷗扒著車窗,給表 弟指認道,「是子琪姐公婆家的- 嚴大哥,你就住這兒的是吧?」 「那個小區太貴了啦…」嚴石無可奈何地搖頭道,「我住附近的惠灣花苑。」 「哦,也還是挺近的嘛!」 「嗯,到裕園也就五六分鍾車程。」 轉入一條幽靜的小街,柏油路變窄了,路旁的梧桐樹卻越發粗壯茂盛。 越過一座小橋,沿著河岸幹淨的林蔭道行進約五六百米,連梧桐樹的枝桠兒 也合攏了,仿佛森林公園般幽靜,一座黑色的鐵柵欄門鑲著塊兒黃銅的牌子刻著 「厓山路168 號」幾個字。 裕園是上海頂級的高檔別墅群之一,總占地面積近百畝,池塘、草地、竹林, 並不刻意攢聚,透露著一股質樸天然的氣息,與其說是住宅區,還不如說是公園 貼切。三十六棟風格各異的別墅錯落有致,反倒更像是秀麗風景的點綴了。 嚴石刷了卡,車開進去,繞了幾個彎,停在一棟三層的巴洛克式小洋樓前。 早有兩個婦人垂手等候,都是三十歲四五歲年紀,系著白色的花邊圍裙,容 貌端莊。 「王姐和羅姐是家裏的傭人。」下了車,靜鷗分別作了介紹,又對嚴石道, 「嚴大哥,你停了車之後就先回去吧!」 「好的!」嚴石對海松招了下手,道,「譚先生,您需要的話,我隨叫隨到。」 梁靜鷗引著父子倆登上台階,女傭人拖著行李箱,穿過擺滿萬年青和瓜葉菊 的立柱長廊。 圓形花廳進去,正對的是青花瓷磚的樓梯,牆壁挂著幾幅油畫,轉角處是彩 繪的玻璃窗。右邊的鋪著琥珀色地板的甬道通往餐廳、廚房。左邊一道浮雕裝飾 的拱門,兩只霁紅釉的落地大花瓶,插著生機盎然的水仙花。 裏面是客廳,鋪著牡丹圖案的地毯,靠南牆擺著台鋼琴,蓋著金色流蘇的布 幔。 「王姐,小臥室收拾好了嗎?」梁靜鷗接過女傭人捧來的紫砂茶盅,問道。 「嗯,已經打掃完了,正在通風。」王姐輕聲答道。 「謝師傅還沒來?」梁靜鷗又問。 「打電話催了,說是在采辦食材,估計一會兒就到。」 梁靜鷗轉向譚海松,體貼地道,「舅舅,您要不要先休息會兒?」 「也不是多累的慌,坐會兒吧,等你外公回來。」譚海松抿了口茶,應道。 「亞鷗,你呢?」梁靜鷗把果盤推到表弟面前。 少年渾身陷在棕褐色的真皮沙發裏,正望著天花板中央繁文缛麗的吊燈發呆, 聽見表姐問話,連忙坐端正了,道:「我也不累- 就是有點餓了…」 「飛機餐很難吃的,是吧?」梁靜鷗笑了笑,吩咐道,「王姐,我帶回來的 餅幹,你去拿些。」 「也還可以,就是量有點少。」 「要了兩份,還不夠他吃的。」譚海松撣了下煙灰,道,「我都不好意思跟 空姐張嘴了。」 「只有幾片熏肉、橙子和西蘭花,兩勺兒米飯…」亞鷗委屈地反駁道。 梁靜鷗望著瘦骨伶仃的表弟,不禁有些心疼,「亞鷗正長身體嘛!」 茶還沒喝完,只聽見兩聲悠長的汽車鳴笛,接著兩個女傭人碎步跑了出去。 「我媽和外公回來了。」梁靜鷗站了起來。 父子倆也跟著她,還沒到花廳,就見一名穿駝色格子西裝的老者推門進來。 老者精神飽滿,銀發宛若山頂的雪冠,拎著頂根紅木手杖,氣勢像是提劍凱 旋的將軍般,舉手投足都透著特別的風度和威儀。兩個衣飾華麗的美貌婦人在左 右攙扶著,年紀稍長的正是譚海榕。 「爺爺!」血濃于水的親情是最天然的情感,沒有人提醒,亞鷗卻石破天驚 地脫口而出,聲音宏亮清晰。 老者銳利的目光倏地投射過來,頓時濁淚縱橫,伸出雙手快步將孫子摟在懷 裏:「哎,乖孩子!」 「爺爺…」亞鷗的也被感染了,眼睛發酸,道。 「好孩子,你爸總算把你平安帶來了!」譚老先生枯瘦的手撫摸著亞鷗的臉 龐,模樣跟曾經的自己那麽相似,萬千往事湧到心口,「我該死啊,當年一走了 之,害你們在小縣城裏受罪…」 亞鷗對于譚家的舊事沒有切身體會,只是突然想起苦命的母親,哽咽著。 「你回來啦,咱姓譚的,就後繼有人了!」譚老先生號啕如雷,像是在發泄 沈積幾十年的憤懑,「再沒誰敢欺負咱了啊…」 「再沒誰敢欺負咱了…」亞鷗念叨著祖父的話,心底的傷疤無意間被觸動, 淚珠兒悄然滾落。 「亞鷗,別哭了…」譚海榕拍著亞鷗的背,又安慰父親道,「爸,亞鷗也回 來了,阖家團圓,該高興才是啊!」 「爸!」譚海松接過父親的手杖,也道,「您要當心身體啊!」 衆人勸撫之下,譚老先生逐漸恢複了平靜,幫亞鷗擦著眼角,憐愛地道, 「亞鷗,我不哭了,你也不哭了。再哭就讓人笑話了!」 客廳裏,譚玉坤向海松和亞鷗引見了白鹭。 她二十七八歲左右,或許還更年輕,容貌姣好,身姿袅娜,正是個綽約的花 信少婦。一襲绛紫色菱形镂空花紋的針織披肩,灰白小格子的喇叭長裙,言談舉 止都帶著養尊處優的閑適和淡然,文靜淑雅如嬌花照水。 海榕和靜鷗都稱呼她「鹭姐」,海松和亞鷗也就跟著叫了。 「大哥,車怎麽樣?」譚海榕從更衣間出來,脫掉了鹦鹉綠的金絲呢絨外套, 爽朗地問道。 「咦,漂亮得很嘞!」譚海松由衷地道,「也穩當得很,跑起來跟抓著柏油 路一樣!」 「呵呵,那是爸去年生日的時候,敲仰真的竹杠,卻基本沒乘過,閑置著怪 可惜的- 爸年紀越大,就越喜歡胡亂要東西!」 姑媽約四十五六歲了,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飽經歲月洗禮的肌膚依舊光滑 潤澤,花容月貌宛似浮世繪中的仕女,渾身透著秋日果實般的成熟。說話的時候 螓首微昂,驕傲地猶如白天鵝,「上海是個勢利場,只認衣裳不認人。你初來乍 到,或許用的著。」 「你姑媽又講我壞話!」譚老先生扭頭朝亞鷗扮了個鬼臉。 滿頭銀發的祖父居然還跟小孩子一樣,亞鷗無言以對,只能咧著嘴傻笑。 「我擺事實而已!」譚海榕捋起白绉綢襯衫的袖筒,撇了父親一眼,道, 「連這別墅也是,當初非要買,卻幾乎一直空著,也就是過年的時候熱鬧些。」 「現在百分之六十五的業務都在大陸,你們到上海,也算有個駐腳的地方嘛!」 譚海榕沒理會,繼續道,「你和亞鷗先住下,不合適的話再換。觀瀾禦景的 樓盤好像還不錯,安妮在那邊才拿了套…」 「安妮又買房子啦?」譚玉坤再次插嘴道,「她在台北的兩套房子也不租售, 分明打麻將輸給我,居然還賴賬…」 「外公,是您作弊好不好?跟鹭姐串通了換牌!」靜鷗忍不住爆料道,「安 妮說一輩子再不跟您打牌,把您拉黑名單了,最討厭作弊的!」 白鹭的俏臉登時通紅了。六七十歲的老先生了,跟孫輩打麻將還作弊?!簡 直令亞鷗哭笑不得。 「誰作弊了?」譚玉坤被外孫女戳破真相,氣急敗壞地辯護道,「你外公好 歹也是德高望重,會跟你們兩個毛丫頭作弊?我小時候考試都沒作弊過,不信你 去問我當年的老師!」 「您都一把胡子了,您老師估計正在陪閻王爺打麻將呢,好一個死無對證!」 梁靜鷗鄙夷地嘟著嘴,道。 「鷗妮,怎麽跟外公說話呢?」一個沈穩有力的中年男聲從客廳外傳來,責 備中含著愛憐。 梁仰真依舊戴著那副名貴的金絲眼鏡,挂著招牌式的溫文爾雅的笑容,濃郁 的書卷氣質撲面而來。 「爸爸!」表姐滿是喜悅之色,飛也似地撲進了姑丈的懷裏。 梁仰真擁抱過女兒,又跟亞鷗父子倆打了招呼,挨著妻子坐進了沙發裏。譚 海榕水眸裏蕩漾著蜜意,溫柔地吻了丈夫的臉頰。 「仰真也回來了,我講兩句話。」譚玉坤收起笑容,端起茶盅潤了下喉嚨, 對海松道,「首先是對你的安排。」 譚海松立刻正襟危坐,洗耳恭聽父親的指示。 「我跟海榕商量了,由你出任酒店集團的總裁。你先跟著曆練,不要嫌委屈。」 譚玉坤一改之前老頑童般的嬉哈,雷霆萬鈞地道。 「不會的,職位其實沒啥。」譚海松誠懇地道,「我還想著從基層做起嘞, 更能全面了解情況。」 「那倒用不著,細枝末節的東西,交給底下人做。」譚玉坤道,「公司跟單 位還是不同,要會抓,也要會放。」 「嗯,是!」譚海松小雞啄米地點頭道。 「你要多向仰真討教。」譚玉坤指了下女婿,「遇事兒也可以找他商量。」 「爸,您把我捧得也太高了。」梁仰真接過話,笑著建議道,「選派幾個可 靠得力的副總裁才是正經的。」 「嗯,我也有此意。」譚玉坤又對女兒道,「海榕,你跟陳星午擬個名單。」 「好的!」譚海榕答應了,又道,「我也說句話啊。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 的水- 譚家的事,本來不該我插手的。」 「從前把我當兒子養,也就算了。現在大哥和您寶貝孫子回來了,我樂得還 政讓位,落個清閑。以後需要我幫忙,自然是義不容辭,但是您老還想把我當苦 力使喚,就要付工錢了!」 「你瞧這丫頭,學會跟我討價了!」譚老先生拿手杖作勢要敲她,笑罵道, 「不要慌著表忠心,沒誰敢動你還!」 海松嗅到了一絲異樣,連忙剖白道:「爸,海榕是逗您呢!我對家裏的事兒 一竅不通,光學也要個三年五載啊。她是家裏的頂梁柱,絕對缺不了她嘞!」 譚老先生要的就是兒子的態度,語氣緩和道,「其次啊,我是希望你盡快續 弦的…」 母親還沒過百日,祖父居然就勸父親再娶。 亞鷗心裏一涼,就想掙脫譚玉坤一直握著他腕子的手。 「玉屏才走,怎麽著也要過一段時間…」譚海松看了眼亞鷗,小聲道。 「逝者已去,活人還要繼續活嘛!」譚玉坤俨然不甚滿意,展臂將白鹭拉進 懷裏,少婦並未任何抗拒,一副小鳥依人的乖巧模樣。 她最多也就比表姐大四五歲,原來竟是祖父的情婦- 父親在融城也有不止一 個女人。譚家男子的風流成性,莫非是遺傳嗎?亞鷗一陣酸楚,可憐起母親來。 「家裏人丁不旺,你才五十幾歲,還能養個一兒半女。」 譚玉坤摩挲著白鹭紅潤的酥手,就像把玩玉器一般,道。 海榕一家三口都是司空見慣的樣子,譚海松卻略覺窘迫,低垂著目光,道: 「嗯,我會考慮的…」 「亞鷗你呢,有沒有女朋友?」 譚玉坤交待完正事兒,又恢複了老頑童的神態,把亞鷗的手放到胸口,狡黠 地對孫子眨眼道。 「哎呀,你別教壞小孩子啦!」白鹭秀眉微蹙,在他腰裏擰了一把,出人意 料地嬌嗔道。 |

- 拗拗女月老(西京十三絕12)
- [學生校園]酒後亂性的學姊
- [不倫戀情]我和年輕漂亮師母的激情
- [職場激情]一個離職的女同事
- [經驗故事]女友逛街試衣被騎
- [人妻熟女]淫妻玉姗
- [科學幻想]催眠秀的陰謀-大雜交
- [人妻熟女]有趣的夫妻
- [經驗故事]HOTEL 艷遇
- [經驗故事]家事
- [學生校園]被國小學生騙喝瀉藥無力反抗
- [職場激情]李英俊的情慾世界
- [職場激情]客串護校男模的尷尬經驗
- [學生校園]女友和她的閨蜜
- [不倫戀情]【姐夫的榮耀】第四十一章 恐嚇
- [職場激情]不能說的秘密
- [職場激情]國資委的故事19~27
- [職場激情](非原創)姐夫的榮耀(六)
- [暴力虐待]迷蹤姦影11_20(絕對經典好看)
- [人妻熟女]龍飛鳳舞小說系列13-18
- [經驗故事]第一次碰撞處女穴
- [不倫戀情]姨媽和表姐們
- [科學幻想]露營——未來篇 全集
- [職場激情]我是第幾個
- [職場激情]前妻的誘惑
- [不倫戀情]我搓揉的鏡中母親的E奶巨乳〔超短篇〕
- [人妻熟女]【天安門邂逅豪乳少婦】
- [職場激情]江蘇省教育廳關于建立高等院校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通知
- [職場激情]妻子姚嘉(妻子的幸福生活)
- [人妻熟女]和女同事做愛
- [職場激情]玉娟(1-3)
- [不倫戀情]跟小妹做愛
- [科學幻想]齊天大聖戰嫦娥、3P鐵扇公主
- [職場激情]昨晚,實現了一次4人聚會
- [人妻熟女]老婆懷孕檢查
- [人妻熟女]《鴨鴨俱樂部》之性愛無限篇
- [人妻熟女]美麗性感的阿姨
- [玄幻仙俠]【我的天下】 31-36 (完) 作者:Michanll&英雄
- [不倫戀情]雞巴曆險記 (2/4)
- [玄幻仙俠]奇魄香魂 (1-100全) (3/33)
- [附圖小說]夜勤病棟-淫虐集中治療室 (1-10章完) (4/4)
- [職場激情]【國航內部年會】 作者:xxs118 (3/4)
- [人妻熟女]副省長女秘書 1-8 (2/3)
- [暴力虐待]瘋狂地獄輪姦1 公車
- [人妻熟女]風流美婦俏女傭 (1/2)
- [不倫戀情]我的巨乳媽媽全裸讓水果店老闆摸奶
- [人妻熟女]我與小姨子的愛情 (1-5)
- [不倫戀情]讓媽媽懷上我的孩子吧!!!!!!
- [不倫戀情]嬸嬸與我
- [學生校園]鋼琴老師!
- [人妻熟女]激情無塵室
- [職場激情]中年男子,中年男人,深褐色
- [職場激情]援交情人
- [職場激情]非禮勿視
- [職場激情]與鄰居美麗少婦的姦情
- [人妻熟女]三十歲熟女
- [不倫戀情]女兒們的後代
- [學生校園]誘騙高中學姐
- [人妻熟女]大嫂和她的好友幫我口交
- [人妻熟女]老婆的群交生活
小說區 隨機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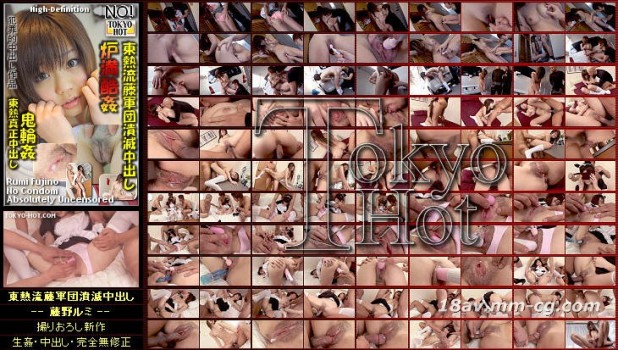







![Bejean On Line 2007-04 [Hassya]- Rio Tsukishima](https://fbhost1.imgstream2.com/s/wp/wp1409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