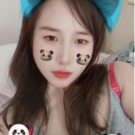小說名稱:[科學幻想]離開農村通行證的代價
劉小婷教授去世了。她是我讀碩士時的指導老師。今年才56歲。劉教授直
到去世還孑然一身。不是她不想愛,不是她不想被愛。只是那一段已成為歷史的
記憶給她的烙印太深,不僅烙壞她的驅體,更烙壞她的人生。
我是在臨畢業時才聽恩師講起,那時她患了子宮癌。我震驚也羞辱這片大地
曾有過這樣的歷史。在恩師顫微微的手給我戴上碩士帽時,送給我一本發黃的日
記。里面記載著這段歷史。她在扉頁貼了張紙,用紅如血色的墨水寫了三行字:
“當我不在人世
你可以公開
歷史不該忘卻“
記住: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所發生的特殊的事件,一個幾乎被社會忘卻了的
真實的故事,歷史有權力讓後人所知,歷史但願不再重演。
——題記
醫院婦科體檢室的里間。一張50公分寬的窄床。
她從她的陰道里緩緩抽出手指,心里壓著的鉛塊更加沉重,她是她今天第八
個被檢者。無一例外,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是陳腐性裂痕,以她的知
識和經驗,她們至少有三年以上性史。
“你不是處女。”女醫生的聲音很輕,輕到只有被檢者能夠聽到。
“阿姨,我是的。”被檢者的聲音也很輕,但很蒼白。
“我是醫生,孩子。”
“求求你,阿姨。這是我唯一……”被檢者“撲通”跪下,頭用力撞在水泥
地面,一個響頭。
沒等她再次撞下,女醫生攙起她:“我知道,孩子。我有個女兒還在農村。
”
女醫生雙眼已經模糊起來,“不知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女醫生拿起那張“工農兵學員推薦表”,在“處女膜”欄重重地劃了一個對
勾。被檢者感激地向女醫生深深鞠了一躬。
她走出醫院。天是湛藍的。可她心在還在流血。黑幕下的記憶留給她太多創
傷。她不會忘卻,也無法忘卻。
☆☆☆☆☆☆☆☆☆☆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那是個崇拜加迷信的年代。
婷婷這年高中畢業。她已是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發育完全成熟。她集合
了父母的全部優點,美的叫人不敢對視。
再美,她也無法留在上海。和千百萬的知識青年一樣的命運,她捲起簡陋的
行李,來到雲南西雙版納靠近邊境的一個農場,和當地農民一起開墾荒山,種植
橡膠樹。不久她所在的農場成為XX軍區XX生產建設兵團的一部分,大批現役
軍人開進到兵團,擔任了由連長以上的全部正職乾部。婷婷興奮了好久,認為自
己已經成為一個軍人。盡管人們稱之為準軍人。
可她永遠不會想到,她的人格和人生會在這片美麗的地方遭到無情的蹂躪。
不幸是從一天早上開始的。
“嘀……嘀嘀……達達!”婷婷在第一聲軍號中便從睡夢中醒來,她以軍人
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襯衣、蹬上長褲和螞蝗套,戴上頭燈,挎上膠刀筐,穿上
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一盞又一盞晃動的頭燈在晃動,現在天還沒有大亮。即使大亮,橡林高
大的陰影也會擋著黎明,只有在陽光普照時橡林才會亮堂。他們每人有一片屬于
自己的林段,婷婷的五百株在橡林深處。每天這時候,婷婷都會害怕,因為有野
豬在這里出沒,她曾聽說有個男知青被野豬一拱嘴就咬掉大腿半邊肉。
“嘩,嘩!”一陣聲響。她哆哆嗦嗦地抬起頭,緊緊攥住鋒利無比的膠刀。
“誰?”她使出全身力氣高喊了一聲,聲音帶著顫抖。
“我,連長。”
隨著聲音望去,她看見一團光亮,戴著頭燈的連長在幫她割膠,她放心了。
連長幾乎天天出現在各個林段中,檢查生產情況或幫助生手、慢手割膠。
婷婷對連長印象很好。連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為人和氣,聽說還是全兵
團的神槍手,她對他充滿敬佩,現在又充滿感激。因為這幾天連長到她這來的時
間特別多,使她可以比平時快一到兩個小時割完膠。
今天又是一樣。她和連長把膠汁並在一處後,準備回去。
連長說:“休息一會吧。”
她點點頭,跟在連長後面來到山頂處的一小塊空地上。連長一上山就把掛在
腰上的雨布鋪開,自己坐下後,讓婷婷坐在他的身邊。
“擦擦汗吧。”連長遞過一條毛巾。
婷婷接過來擦去額頭的汗珠,揮舞毛巾驅趕了一下蚊子,又尋找著有無螞蝗
爬上來。這時她覺得有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幫她驅趕什麼。她很
感謝,側臉衝連長笑笑。連長也在笑,眼中燃燒著一股她從未見到過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連長為什麼會這樣笑。
直到連長的手挪到她胸前,試圖解開襯衣扣子時她才開始恍惚。
和往常一樣,婷婷今天依舊沒有戴胸罩。一方面是因為西雙版納地區的炎熱,
更重要的是,她們被要求和當地的農民一樣,“接受再教育”。
婷婷的乳房比連長在軍營附近見到過的那些農村姑娘的要白嫩和誘人得多。
從家里帶來的白“的確涼”襯衣,本身就呈現半透明狀態,隱隱約約可看到
粉色乳暈。乾活時汗水浸濕襯衣,使得乳房輪廓更為明顯,前端半個乳房就是不
脫掉襯衣也看得清請楚楚。
婷婷用手捂住衣襟,連長用手扳開她的手。她用力掙扎,連長不再溫柔,朝
她使勁抽了一個耳光。她被打懵了,不懂連長為什麼要打她。
接下來的事更讓她不明白。連長飛快地脫下自己的衣褲,赤條條地站在婷婷
面前,一手抓住她的頭髮,一手拿著自己的雞吧,威嚴地命令道:“把口張開!
”
婷婷第一次看到成熟男人的雞吧,臉立刻羞得通紅。沒等她有任何想法,威
嚴地命令又重復了一道:“把口張開!”緊接著,那只拿著雞吧的手空出來,朝
已有五個手掌印的臉上又是一巴掌!
婷婷不想再挨巴掌,張開嘴。
“張大點!”婷婷盡力張大。
連長握住雞吧,捅進她的口中。抓住她的頭髮的那只手,移到後腦使勁往自
己的胯部一送,婷婷感到喉嚨管被連長的雞吧捅破了,差點閉過氣去。她用雙手
抵住連長的大腿,想推開他。無論怎樣用力都是白費。
連長的雞吧開始在她的口中抽送,正在她感到難受時,臉上又挨了一巴掌:
“他媽的!還是從上海來的,雞吧都不會吃。”雞吧在她的口中變得越來越長越
來越粗,攪得她的眼淚和鼻涕都流了出來,此刻她覺得比死了還難受。
雞吧離開了她已失去知覺的嘴巴。她松了口氣,以為結束了。沒待她喘第二
口氣,連長雙手抓住她的衣襟用力一扯,她那豐滿而挺立的雪白乳房和鮮嫩的乳
頭即刻彈射出來。她下意識地用手抱住。
“把手拿開!”聲音依舊是威嚴的,而且威嚴得有些沙啞。婷婷不敢不拿開。
婷婷被平攤在地上,仰面朝上。一個乳頭被連長咬進了嘴里,一陣一陣的疼
痛傳來,她不得不求連長輕點。兩個乳頭被交替咬著,淚水順著眼角不停流淌,
流在頭髮上,再滴到連長帶來的那塊雨布上。
連長叉開雙腿把全身的重量都傾壓在她下半身上。她扭動了一下,希望可以
舒服一點。
“怎麼?發騷了?想要了?好!”一只手熟練地解開了婷婷的褲帶,並把手
伸進她雙腿之間。婷婷頓時嚇呆了。她知道連長要乾什麼,可她只能目瞪口呆,
束手無策,她不敢呼叫。
她心里壓力太大了:連長的權勢,紅色的領章、紅色的帽徽,充分顯示出一
種威嚴!在那個XX軍的威信和地位處于巔峰的年代,說XX軍半句壞話,就被
扣上“毀我長城”的帽子,會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連長像打戰一樣,舉起硬如刺刀的雞吧,一下捅進婷婷的嫩穴,如猛獸吞食
小動物一樣瘋狂地占有了婷婷。婷婷本能地抵抗了幾下,但那樣無力,幾乎是眼
睜睜地忍受著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體時的痛苦和傷痛。
完事之後,連長撫摸著她,向她許了不少願,入團、入黨、提乾等等。她一
句沒聽進去,只掉淚。連長拍了拍身上粘著的泥土和碎葉,心滿意足地站起來,
收起了雨布,用樹葉擦了擦自己的雞吧,擦去留在上面的處女血痕和污物,哼著
不知名的小調丟下婷婷揚長而去。
失去貞操,對婷婷而言,她可能不會一輩子耿耿于懷,因為貞操並不值錢。
值錢的是愛,可婷婷在失去貞操時得到的不敢聲張的強暴卻不是愛!
連長又來找她,她拼死拒絕。連長這次倒沒動粗。但第二天婷婷便被調到二
十里外的一個小水庫去管閘門,每天早去晚歸。頂星星披月亮她不怕,她怕的是
陪伴她的當地兩個比連長更魁梧的壯漢,整天四只眼睛就只盯住她的胸部和檔部。
一星期後她屈服了,給了連長一個暗示。連長陪她看了一天水閘,在水閘邊
當著兩個壯漢脫掉她的褲子,第二天她就被調回。
此後,婷婷成了連長泄欲的工具。
☆☆☆☆☆☆☆☆☆☆
兩年後,來了個文件,知青可以調換地區。在父親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婷婷
轉到另一個沒有軍人的生產隊。
她報到的第一天,生產隊長問她:“為什麼要轉到我們這來?”
她說:“我在那里不適應。”
隊長問:“怎麼個不適應?”
她說:“我,我……”她不知該怎麼說,也沒想到會有這一問。
“是不是,那個,那個事……,哈哈,還不好意思呢,轉隊都為這事。好,
來我們這好好乾,啊!”隊長邪淫的目光盯住她高矗的胸部。
她躲開那十分熟悉的目光,心中又害怕了,感覺是逃出了虎窩掉進了狼窩。
…………
“我必須離開這里。”這是婷婷唯一的想法。
夜深人靜,幾顆稀疏的星掛在天空。趁著漆黑,婷婷有些麻木地推開生產隊
長家的門,一步一步沉重萬分地走了進去。
“隊長……”婷婷叫了一聲,看到隊長色迷迷的目光,頓住了。
“哦,婷婷呀。快來坐坐!”桌上還剩半瓶二鍋頭,邊上一小盤花生米。
婷婷緩緩的走過去,在隊長的對面半個屁股挨在長凳上。
“來,喝一杯!”隊長往他自己的杯中倒滿,遞到婷婷跟前,酒精過度已使
他的眼睛有些昏濁。
“不,我不會喝。您自己喝吧。”婷婷把杯子推回到隊長那邊。
“什麼?不會喝?敢撥我的面子!”隊長突然提高聲調,把婷婷嚇了一跳。
“看看!”隊長從桌下不知什麼地方拿出個黑色的髒兮兮的包來,他拉開拉
鏈,掏出一張紙和個小匣子,婷婷知道那是張工農兵學員推薦表格,匣子里裝的
是生產隊的大印。
婷婷伸手端過酒杯,一仰脖杯底朝天。
“咳……咳咳……”劇烈的咳嗽把婷婷的那張臉憋得通紅通紅。
“不急,慢慢喝,有的是時間。”隊長走到婷婷面前,拍打起她的後背,接
著從上到下摸起來一直摸到屁股。
婷婷不敢閃躲,她清楚隊長要什麼。
“隊長,我先把表填了吧?”婷婷想在隊長還算明白時辦完這件正事。
“好,好。到里面去填。”隊長收起工農兵學員推薦表和那顆印,夾起包先
動身。
婷婷雙目無神,象一個被送上祭台的羔羊。眼淚流了出來。她沒有辦法不跟
進去。
里屋的一盞油燈閃閃爍爍,隊長望著婷婷粗魯地笑著,婷婷心里陣陣發毛。
隊長一把扯開婷婷的衣衫,用那雙長滿死繭,粗糙得可以搓掉一層皮的大手,
毫不客氣的揉摸那一對發育成熟的乳房,滿口酒氣直向婷婷嘴上湊。婷婷沒敢把
臉扭開,任由那張臭嘴挨上自己的唇皮,再挺進到自己的嘴里。
他把她推倒在充滿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她沒有喊叫,怕人聽到,只是心
和下體一同疼痛著。她今天還在經期還沒乾淨,可隊長說,錯過今天沒明天。他
的身體本來就十分強壯,酒精的作用使他更為威猛。
“今天一定要你記住我,記住我一輩子!”隊長把婷婷翻了個身。她不知道
她要乾什麼,為什麼說話這麼咬牙切齒。
“把屁股撅起來!”隊長的話讓婷婷膽寒,她明白他想乾什麼了。
“隊長,求求你,就在前面吧!後面從來沒有過……”
“就是沒有過老子才要,有過老子還不搞呢!”隊長朝婷婷白白的屁股上狠
狠的扇了一巴掌,嫩嫩的屁股上立即印出五道血痕。隊長朝他雞吧上吐了幾口口
水,把一根手指放到嘴里濕潤了一下,就捅進了婷婷的屁眼。
“啊!!”婷婷此時顧不上是否有人會聽見,確實太疼了。
“求你別在後面搞了,實在是不行了。”婷婷還在乞求,希望隊長發發善心。
可她馬上就感到屁眼插入更粗的東西,鑽心的疼痛令她趴下了。
“起來!小騷婊子!把你的騷屁股給老子撅起來!再不撅,老子不蓋章!”
隊長的話不僅僅是威脅,他有這個權力,而且誰也不會過問的權力。
婷婷咬牙撅起屁股,只希望他盡快完事。可他正在興頭,搞得沒完沒了,邊
搞邊用一只手摸那垂得很下的乳房,邊用一只手抽打已滿是血痕的屁股。婷婷只
能咬牙堅持,唇皮已被咬破,血從嘴上滴到齷齪的床單上。
終于搞完了。婷婷從床上站起來時全身疼痛,她滯重地穿著衣服時,生產隊
將血紅的大印蓋在了表格上面。婷婷接過招工表,眼淚又掉下來。她看著那鮮紅
的大印,看著床單上印著的從她體內流出的血痕,都是一樣的鮮紅。她還要到大
隊、公社去流淚、去流血……
婷婷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不!絕不!僅僅是以肉體為代價嗎?!
☆☆☆☆☆☆☆☆☆☆
多余的交代:
一九七四年的某天。雲南河口縣。建設兵團第十六團駐地。十幾挺輕機槍和
兩挺重機槍戒嚴。這是一個執行中央關于打擊殘害知識青年的正式文件精神,由
軍事法庭主持的公審大會。十幾個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幾名持槍的戰
士排成一排,平舉自動步槍,在一聲命令中,扣動扳機。每人都放空了槍中的子
彈後,戰士們跑步離開刑場,兩個提手槍的公安走過去,對著未死的犯人補槍。
被審判的全部是XX軍現役軍官!
到去世還孑然一身。不是她不想愛,不是她不想被愛。只是那一段已成為歷史的
記憶給她的烙印太深,不僅烙壞她的驅體,更烙壞她的人生。
我是在臨畢業時才聽恩師講起,那時她患了子宮癌。我震驚也羞辱這片大地
曾有過這樣的歷史。在恩師顫微微的手給我戴上碩士帽時,送給我一本發黃的日
記。里面記載著這段歷史。她在扉頁貼了張紙,用紅如血色的墨水寫了三行字:
“當我不在人世
你可以公開
歷史不該忘卻“
記住: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所發生的特殊的事件,一個幾乎被社會忘卻了的
真實的故事,歷史有權力讓後人所知,歷史但願不再重演。
——題記
醫院婦科體檢室的里間。一張50公分寬的窄床。
她從她的陰道里緩緩抽出手指,心里壓著的鉛塊更加沉重,她是她今天第八
個被檢者。無一例外,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是陳腐性裂痕,以她的知
識和經驗,她們至少有三年以上性史。
“你不是處女。”女醫生的聲音很輕,輕到只有被檢者能夠聽到。
“阿姨,我是的。”被檢者的聲音也很輕,但很蒼白。
“我是醫生,孩子。”
“求求你,阿姨。這是我唯一……”被檢者“撲通”跪下,頭用力撞在水泥
地面,一個響頭。
沒等她再次撞下,女醫生攙起她:“我知道,孩子。我有個女兒還在農村。
”
女醫生雙眼已經模糊起來,“不知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女醫生拿起那張“工農兵學員推薦表”,在“處女膜”欄重重地劃了一個對
勾。被檢者感激地向女醫生深深鞠了一躬。
她走出醫院。天是湛藍的。可她心在還在流血。黑幕下的記憶留給她太多創
傷。她不會忘卻,也無法忘卻。
☆☆☆☆☆☆☆☆☆☆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那是個崇拜加迷信的年代。
婷婷這年高中畢業。她已是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發育完全成熟。她集合
了父母的全部優點,美的叫人不敢對視。
再美,她也無法留在上海。和千百萬的知識青年一樣的命運,她捲起簡陋的
行李,來到雲南西雙版納靠近邊境的一個農場,和當地農民一起開墾荒山,種植
橡膠樹。不久她所在的農場成為XX軍區XX生產建設兵團的一部分,大批現役
軍人開進到兵團,擔任了由連長以上的全部正職乾部。婷婷興奮了好久,認為自
己已經成為一個軍人。盡管人們稱之為準軍人。
可她永遠不會想到,她的人格和人生會在這片美麗的地方遭到無情的蹂躪。
不幸是從一天早上開始的。
“嘀……嘀嘀……達達!”婷婷在第一聲軍號中便從睡夢中醒來,她以軍人
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襯衣、蹬上長褲和螞蝗套,戴上頭燈,挎上膠刀筐,穿上
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一盞又一盞晃動的頭燈在晃動,現在天還沒有大亮。即使大亮,橡林高
大的陰影也會擋著黎明,只有在陽光普照時橡林才會亮堂。他們每人有一片屬于
自己的林段,婷婷的五百株在橡林深處。每天這時候,婷婷都會害怕,因為有野
豬在這里出沒,她曾聽說有個男知青被野豬一拱嘴就咬掉大腿半邊肉。
“嘩,嘩!”一陣聲響。她哆哆嗦嗦地抬起頭,緊緊攥住鋒利無比的膠刀。
“誰?”她使出全身力氣高喊了一聲,聲音帶著顫抖。
“我,連長。”
隨著聲音望去,她看見一團光亮,戴著頭燈的連長在幫她割膠,她放心了。
連長幾乎天天出現在各個林段中,檢查生產情況或幫助生手、慢手割膠。
婷婷對連長印象很好。連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為人和氣,聽說還是全兵
團的神槍手,她對他充滿敬佩,現在又充滿感激。因為這幾天連長到她這來的時
間特別多,使她可以比平時快一到兩個小時割完膠。
今天又是一樣。她和連長把膠汁並在一處後,準備回去。
連長說:“休息一會吧。”
她點點頭,跟在連長後面來到山頂處的一小塊空地上。連長一上山就把掛在
腰上的雨布鋪開,自己坐下後,讓婷婷坐在他的身邊。
“擦擦汗吧。”連長遞過一條毛巾。
婷婷接過來擦去額頭的汗珠,揮舞毛巾驅趕了一下蚊子,又尋找著有無螞蝗
爬上來。這時她覺得有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幫她驅趕什麼。她很
感謝,側臉衝連長笑笑。連長也在笑,眼中燃燒著一股她從未見到過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連長為什麼會這樣笑。
直到連長的手挪到她胸前,試圖解開襯衣扣子時她才開始恍惚。
和往常一樣,婷婷今天依舊沒有戴胸罩。一方面是因為西雙版納地區的炎熱,
更重要的是,她們被要求和當地的農民一樣,“接受再教育”。
婷婷的乳房比連長在軍營附近見到過的那些農村姑娘的要白嫩和誘人得多。
從家里帶來的白“的確涼”襯衣,本身就呈現半透明狀態,隱隱約約可看到
粉色乳暈。乾活時汗水浸濕襯衣,使得乳房輪廓更為明顯,前端半個乳房就是不
脫掉襯衣也看得清請楚楚。
婷婷用手捂住衣襟,連長用手扳開她的手。她用力掙扎,連長不再溫柔,朝
她使勁抽了一個耳光。她被打懵了,不懂連長為什麼要打她。
接下來的事更讓她不明白。連長飛快地脫下自己的衣褲,赤條條地站在婷婷
面前,一手抓住她的頭髮,一手拿著自己的雞吧,威嚴地命令道:“把口張開!
”
婷婷第一次看到成熟男人的雞吧,臉立刻羞得通紅。沒等她有任何想法,威
嚴地命令又重復了一道:“把口張開!”緊接著,那只拿著雞吧的手空出來,朝
已有五個手掌印的臉上又是一巴掌!
婷婷不想再挨巴掌,張開嘴。
“張大點!”婷婷盡力張大。
連長握住雞吧,捅進她的口中。抓住她的頭髮的那只手,移到後腦使勁往自
己的胯部一送,婷婷感到喉嚨管被連長的雞吧捅破了,差點閉過氣去。她用雙手
抵住連長的大腿,想推開他。無論怎樣用力都是白費。
連長的雞吧開始在她的口中抽送,正在她感到難受時,臉上又挨了一巴掌:
“他媽的!還是從上海來的,雞吧都不會吃。”雞吧在她的口中變得越來越長越
來越粗,攪得她的眼淚和鼻涕都流了出來,此刻她覺得比死了還難受。
雞吧離開了她已失去知覺的嘴巴。她松了口氣,以為結束了。沒待她喘第二
口氣,連長雙手抓住她的衣襟用力一扯,她那豐滿而挺立的雪白乳房和鮮嫩的乳
頭即刻彈射出來。她下意識地用手抱住。
“把手拿開!”聲音依舊是威嚴的,而且威嚴得有些沙啞。婷婷不敢不拿開。
婷婷被平攤在地上,仰面朝上。一個乳頭被連長咬進了嘴里,一陣一陣的疼
痛傳來,她不得不求連長輕點。兩個乳頭被交替咬著,淚水順著眼角不停流淌,
流在頭髮上,再滴到連長帶來的那塊雨布上。
連長叉開雙腿把全身的重量都傾壓在她下半身上。她扭動了一下,希望可以
舒服一點。
“怎麼?發騷了?想要了?好!”一只手熟練地解開了婷婷的褲帶,並把手
伸進她雙腿之間。婷婷頓時嚇呆了。她知道連長要乾什麼,可她只能目瞪口呆,
束手無策,她不敢呼叫。
她心里壓力太大了:連長的權勢,紅色的領章、紅色的帽徽,充分顯示出一
種威嚴!在那個XX軍的威信和地位處于巔峰的年代,說XX軍半句壞話,就被
扣上“毀我長城”的帽子,會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連長像打戰一樣,舉起硬如刺刀的雞吧,一下捅進婷婷的嫩穴,如猛獸吞食
小動物一樣瘋狂地占有了婷婷。婷婷本能地抵抗了幾下,但那樣無力,幾乎是眼
睜睜地忍受著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體時的痛苦和傷痛。
完事之後,連長撫摸著她,向她許了不少願,入團、入黨、提乾等等。她一
句沒聽進去,只掉淚。連長拍了拍身上粘著的泥土和碎葉,心滿意足地站起來,
收起了雨布,用樹葉擦了擦自己的雞吧,擦去留在上面的處女血痕和污物,哼著
不知名的小調丟下婷婷揚長而去。
失去貞操,對婷婷而言,她可能不會一輩子耿耿于懷,因為貞操並不值錢。
值錢的是愛,可婷婷在失去貞操時得到的不敢聲張的強暴卻不是愛!
連長又來找她,她拼死拒絕。連長這次倒沒動粗。但第二天婷婷便被調到二
十里外的一個小水庫去管閘門,每天早去晚歸。頂星星披月亮她不怕,她怕的是
陪伴她的當地兩個比連長更魁梧的壯漢,整天四只眼睛就只盯住她的胸部和檔部。
一星期後她屈服了,給了連長一個暗示。連長陪她看了一天水閘,在水閘邊
當著兩個壯漢脫掉她的褲子,第二天她就被調回。
此後,婷婷成了連長泄欲的工具。
☆☆☆☆☆☆☆☆☆☆
兩年後,來了個文件,知青可以調換地區。在父親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婷婷
轉到另一個沒有軍人的生產隊。
她報到的第一天,生產隊長問她:“為什麼要轉到我們這來?”
她說:“我在那里不適應。”
隊長問:“怎麼個不適應?”
她說:“我,我……”她不知該怎麼說,也沒想到會有這一問。
“是不是,那個,那個事……,哈哈,還不好意思呢,轉隊都為這事。好,
來我們這好好乾,啊!”隊長邪淫的目光盯住她高矗的胸部。
她躲開那十分熟悉的目光,心中又害怕了,感覺是逃出了虎窩掉進了狼窩。
…………
“我必須離開這里。”這是婷婷唯一的想法。
夜深人靜,幾顆稀疏的星掛在天空。趁著漆黑,婷婷有些麻木地推開生產隊
長家的門,一步一步沉重萬分地走了進去。
“隊長……”婷婷叫了一聲,看到隊長色迷迷的目光,頓住了。
“哦,婷婷呀。快來坐坐!”桌上還剩半瓶二鍋頭,邊上一小盤花生米。
婷婷緩緩的走過去,在隊長的對面半個屁股挨在長凳上。
“來,喝一杯!”隊長往他自己的杯中倒滿,遞到婷婷跟前,酒精過度已使
他的眼睛有些昏濁。
“不,我不會喝。您自己喝吧。”婷婷把杯子推回到隊長那邊。
“什麼?不會喝?敢撥我的面子!”隊長突然提高聲調,把婷婷嚇了一跳。
“看看!”隊長從桌下不知什麼地方拿出個黑色的髒兮兮的包來,他拉開拉
鏈,掏出一張紙和個小匣子,婷婷知道那是張工農兵學員推薦表格,匣子里裝的
是生產隊的大印。
婷婷伸手端過酒杯,一仰脖杯底朝天。
“咳……咳咳……”劇烈的咳嗽把婷婷的那張臉憋得通紅通紅。
“不急,慢慢喝,有的是時間。”隊長走到婷婷面前,拍打起她的後背,接
著從上到下摸起來一直摸到屁股。
婷婷不敢閃躲,她清楚隊長要什麼。
“隊長,我先把表填了吧?”婷婷想在隊長還算明白時辦完這件正事。
“好,好。到里面去填。”隊長收起工農兵學員推薦表和那顆印,夾起包先
動身。
婷婷雙目無神,象一個被送上祭台的羔羊。眼淚流了出來。她沒有辦法不跟
進去。
里屋的一盞油燈閃閃爍爍,隊長望著婷婷粗魯地笑著,婷婷心里陣陣發毛。
隊長一把扯開婷婷的衣衫,用那雙長滿死繭,粗糙得可以搓掉一層皮的大手,
毫不客氣的揉摸那一對發育成熟的乳房,滿口酒氣直向婷婷嘴上湊。婷婷沒敢把
臉扭開,任由那張臭嘴挨上自己的唇皮,再挺進到自己的嘴里。
他把她推倒在充滿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她沒有喊叫,怕人聽到,只是心
和下體一同疼痛著。她今天還在經期還沒乾淨,可隊長說,錯過今天沒明天。他
的身體本來就十分強壯,酒精的作用使他更為威猛。
“今天一定要你記住我,記住我一輩子!”隊長把婷婷翻了個身。她不知道
她要乾什麼,為什麼說話這麼咬牙切齒。
“把屁股撅起來!”隊長的話讓婷婷膽寒,她明白他想乾什麼了。
“隊長,求求你,就在前面吧!後面從來沒有過……”
“就是沒有過老子才要,有過老子還不搞呢!”隊長朝婷婷白白的屁股上狠
狠的扇了一巴掌,嫩嫩的屁股上立即印出五道血痕。隊長朝他雞吧上吐了幾口口
水,把一根手指放到嘴里濕潤了一下,就捅進了婷婷的屁眼。
“啊!!”婷婷此時顧不上是否有人會聽見,確實太疼了。
“求你別在後面搞了,實在是不行了。”婷婷還在乞求,希望隊長發發善心。
可她馬上就感到屁眼插入更粗的東西,鑽心的疼痛令她趴下了。
“起來!小騷婊子!把你的騷屁股給老子撅起來!再不撅,老子不蓋章!”
隊長的話不僅僅是威脅,他有這個權力,而且誰也不會過問的權力。
婷婷咬牙撅起屁股,只希望他盡快完事。可他正在興頭,搞得沒完沒了,邊
搞邊用一只手摸那垂得很下的乳房,邊用一只手抽打已滿是血痕的屁股。婷婷只
能咬牙堅持,唇皮已被咬破,血從嘴上滴到齷齪的床單上。
終于搞完了。婷婷從床上站起來時全身疼痛,她滯重地穿著衣服時,生產隊
將血紅的大印蓋在了表格上面。婷婷接過招工表,眼淚又掉下來。她看著那鮮紅
的大印,看著床單上印著的從她體內流出的血痕,都是一樣的鮮紅。她還要到大
隊、公社去流淚、去流血……
婷婷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不!絕不!僅僅是以肉體為代價嗎?!
☆☆☆☆☆☆☆☆☆☆
多余的交代:
一九七四年的某天。雲南河口縣。建設兵團第十六團駐地。十幾挺輕機槍和
兩挺重機槍戒嚴。這是一個執行中央關于打擊殘害知識青年的正式文件精神,由
軍事法庭主持的公審大會。十幾個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幾名持槍的戰
士排成一排,平舉自動步槍,在一聲命令中,扣動扳機。每人都放空了槍中的子
彈後,戰士們跑步離開刑場,兩個提手槍的公安走過去,對著未死的犯人補槍。
被審判的全部是XX軍現役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