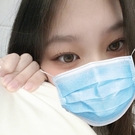小說名稱:[玄幻仙俠]奇魄香魂 (1-100全) (27/33)
第八十一回 孑孑千秋夢
虛竹在後追那老和尚,見他手提二屍,邁開大步,東一轉,西一拐,如淩虛
而行,直往寺後而去。虛竹加快腳步,奮力急奔,眼見距那老和尚的背後只有了
兩三丈之遙,卻無論如何也追趕不上。
到了林間一處平曠之地,老和尚將兩具屍身放在一株樹下,將其都擺成盤膝
而坐的姿勢,他坐去二屍後,雙掌分別抵住兩個身背。
虛竹趕到時,老和尚似在自語:「奔走一程,他們的血脈也該活動了。」
虛竹心下一凜:「哪有將人打死再救活之理?」
接著,二奴氣籲籲趕來,立在主人身後。
老和尚開始擺掌在屍身上不住拍擊,二屍頭頂之上忽然冒出縷縷白氣,越來
越濃,過了一盞茶時分,兩個屍身同時微微顫動,慢慢睜開眼來。
虛竹驚奇之極,能夠叫心不跳而人又不死,實是聞所未聞。
老和尚站去丁春秋和蘇星河面前,問道:「你們可還有什麼放不下?」
丁春秋和蘇星河互視一眼,一齊向老和尚跪下,神情與之前大不一樣。
虛竹更加驚奇,卻不知此二人已由生到死、由死到生地走了一回,雖然只有
短短時間,但其中種種經歷感覺,凡人只有死後才能得以體驗,其情其狀,實非
世間言語所能描述。
蘇星河道:「弟子號稱神醫,一生救治過不少人,也有許多見死不救,有時
洋洋得意,有時暗暗內疚。現下看來,救與不救,醫與不醫,皆世間空幻,唯有
佛門慧根方能得識,弟子懇請師父收錄。」
老和尚微微點頭,轉向蹙眉沈思的丁春秋,笑道:「歷經一生一死,生死符
即已無用,施主現下去哪裡,這就請便吧。」
丁春秋似乎一驚,面露迷惘。
「我……我武功已失,生平殺人百數,死後那些人皆來復仇索命,我實不知
能逃到哪裡去?求師父收為弟子,救我跳出火坑。」
老和尚哈哈笑道:「善哉,善哉!佛門隨緣而度,你們想要為僧,須求寺中
的大師們剃度。」說罷,從虛竹手裡輕輕拿過掃帚,似乎隨意道:「你們且隨我
掃地去吧。」
丁春秋和蘇星河都是一愣,但知老和尚的話必大有深意。
虛竹當然亦不知其意,但此時對老和尚欽佩之至,不敢出聲,帶著二奴悄悄
隨在老和尚的身後,心想:「他只輕輕一掌便可將人收服,叫丁春秋這等惡人也
死心塌地,比生死符還要厲害十倍,不知他肯不肯教我,我去拍一拍阿朱,順手
也拍一下那個紅發妖女,叫她們兩個都哭著求我收留,最好不過!」
幾人回到寺前,遠遠見到人群後,老和尚將掃帚遞給丁春秋。
「你去吧。」
丁春秋躬身接過掃帚,雖有所悟,可無法像老和尚那樣旁若無人得在人群中
掃來掃去,而是躲去僻靜處,藏頭掃起。
老和尚向蘇星河道:「你也去吧。」
蘇星河面露疑惑,攤開雙手,意即沒有掃帚。
老和尚微笑道:「掃地即掃心,當下便是掃帚,我已給了你,還不快去!」
蘇星河一怔之後,歡欣鼓舞而去,伏到青石路上將落葉一葉一葉拾起,專心
致志,毫無旁騖。
此刻,虛竹已穿過人群,即大吃一驚,見喬峰跪在玄慈身前,衣上、頭上、
臉上,到處都是唾沫痰漬,醃臢不堪,慘不忍睹,幾乎瞧不清面目。
「大哥?」
虛竹吃驚叫了聲,快步到喬峰身旁,不知他因何而此。
段譽也從人中穿出,喜叫道:「三弟,你安然無事,真是太好了。」然後向
眾人道:「現下我大哥需要療傷,再有哪位英雄想要洩憤,向我唾來好了。」
段譽向來好潔,說出此話,實是下了好大決心,語意甚誠。
喬峰站起,向一名契丹武士要過酒囊,打開囊塞,舉在頭頂,用酒水淋去了
頭臉上的汙漬,然後仰頭喝了一口,隨即撲哧一聲,連血帶酒噴了出來,他受傷
甚重,這口酒居然壓不下,便將酒囊一扔,捂著胸口道:「謝二弟、三弟,現今
大哥已無牽掛,唯有銘記兄弟之間的恩情!」說到這裡,哈哈一笑,向眾人朗聲
道:「我喬峰今日過後,與江湖再無恩怨,也再不踏入中原半步。現下哪位仍覺
不解恨,盡管出來比劃,喬峰自當奉陪。」
肅靜了好一會兒,終有一人走了出來,瞧著他們兄弟三人,遲疑著不敢冒險
一試,自知絕不是對手,只好滿面羞慚退了回去。
這時,一夥人從山下跑來,慌張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官兵來了,堵著
路口,密密麻麻,也不知來了多少。」
眾豪登時紛亂起來,有人叫道:「大家慌什麼,官兵向來是虛張聲勢,我們
不走大路,四散沖出,他們自拿我們沒有辦法。」
石清慢慢走出人群,眾豪一見,漸漸噤聲。石清站定,皺眉道:「這位兄弟
說的不錯,但官兵明知我武林大會,仍來肆意挑釁,欺各位英雄太甚,我們一再
示弱,官府以後更要猖狂無比。」
當即有人呼應道:「石盟主說的不錯,我們人人以一當十,再多的官兵也殺
他個屁滾尿流,叫朝廷再不敢小覷我們。」
此語一出,越來越多的人舉起了兵器,揮舞叫嚷。
玄寂走出道:「阿彌陀佛!現下情況不明,絕不可擅起干戈。」
石清轉向玄寂道:「大師說的是,請布下少林羅漢陣,保護我等下山。」
玄寂吃驚道:「這個……少林寺乃方外之地,濟世之所,自始以來從不輕易
與朝廷為敵。」
石清微微一笑,大聲道:「保護在場眾位英雄的身家性命,總不會是違背了
我佛降妖伏魔的本義了吧?」
玄寂一時無言以對,眾豪也頃刻消聲,靜候玄寂表態。
忽然清楚傳來一聲:「唉!慕容施主,你目睹他們兩個互相搏斗,怎不出來
解釋清楚?」
眾人望去,說話的是那個掃地的老和尚,正看著玄慈的屍身不住搖頭。眾人
目光紛紛轉向慕容復,此際除了他,場中再無慕容氏。
慕容復因自己「春光曝現」,躲在角落仍羞慚不已,見眾人望來,登時滿臉
通紅,不得已道:「他們之間三十多年前的恩怨,我怎能解釋清楚?」眾人一聽
皆覺如此,三十多年前,慕容復大概還未出生,怎會牽涉此事?
老和尚擡起茫然無神的眼珠,目光沿著圍成一圈的人群向慕容復尋去。眾人
見他目光遲鈍,直如視而不見其物,卻又似自己心中所藏的秘密,每一件都被他
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心中發毛,周身大不自在。
老和尚將目光轉到慕容復臉上,只停了一停,便佝僂下身子緩行幾步,面向
石清道:「老衲已記不清那是多少年前,那時,玄慈方丈剛入我佛門,他與你在
藏經閣前會面,說了一些事,慕容施主可否記得?」
石清沈默片刻,不動聲色道:「在下不知法師說些什麼?」
老和尚搖搖頭,嘆道:「是啊,時間有些久了,當時你們都蒙著面,但老衲
識人,不記其面,只記其骨。人的一生,骨相要比面相可靠多了,因此老衲通常
不會認錯,你們一個自稱路雲天,另一個自稱慕容興。」
眾人哄得議論紛紛,路雲天,一代大俠,當年名震天下,而慕容興在慕容博
隱退後,成為姑蘇慕容的年輕掌門人,二人當時的名頭就如當今的「北喬峰、南
慕容」一般,但二人突然同時銷聲匿跡,成為江湖中的一件懸案。今日卻從一個
看似瘋癲呆傻的老和尚口中說出,且指名道姓,豈不駭人聽聞?
石清又沈默一會兒,冷笑一聲,向玄寂道:「大師,在下對荒謬的道聽途說
並不關心。現下官兵圍攻,江湖形勢危急,少林顧及自保,不願出手相助,也是
情有可緣,但請約束屬僧,不要擾亂視聽!」
石清說到最後,聲音發顫,顯然已經發怒。
人群中,忽然又傳來一聲:「依我看,擾亂視聽的,實是另有其人!」
阿朱走出人圈,手裡舉起那兩封書信,接著說道:「這裡有兩份書信,一封
是三十年前慕容興所書,另一封是近日寫給喬大哥的匿名書信,大家看,這兩份
書信的筆跡完全相同,難道是慕容興陰魂不散,給喬大哥寫了這封信?」
阿朱說著向喬峰走去,人影一閃,夢中人向她搶去。喬峰瞧得清楚,忙出掌
攔阻,剛一發力,便咳出一口血來,而他身旁的虛竹和段譽,機靈不足,待發覺
不妙時,夢中人已經到了阿朱身後。
阿朱練了北冥神功的療傷篇,不僅治好了內傷,應機也大勝從前,感到身後
傳來異風,頭也不回,向後擺手發力,趁勢踏出淩波微步,隨即捂著小腹,不由
一個趔趄,她懷有身孕,猛一催動真氣,小腹便是一痛,吃驚回頭,見夢中人在
身後高舉著一只手臂,身子前傾卻動彈不得,好似被什麼無形之物阻住,手指裡
捏著一根熠熠閃光的細針。
這時,虛竹的天山六陽掌和喬峰的降龍十八掌,都已發向夢中人的後心。
那老和尚站在幾丈遠處,原本已伸出一只手,此時將雙臂合抱,便似推出了
一堵無形高牆,擋在夢中人身後。天山六陽掌和降龍十八掌撞在這堵牆上,登時
無影無蹤,同時消於無形。
喬峰咳嗽著驚異之至。玄寂默念阿彌陀佛,心想這般潛運神功,先是定住了
夢中人的詭異身法,再又阻住了喬峰二人那排山倒海的掌力,莫非這位自己從未
留意的老僧,竟是菩薩化身,否則怎有如此神通?
老和尚收回雙手,緩緩合什,誦道:「陳彌陀佛,佛門善地,眾位施主不可
妄動無明。」
夢中人嗖地退回原處,她這一進一退,都是無影無聲。阿朱瞧得害怕,忙走
幾步,躲到老和尚身後,向玄寂遞過那兩封信。
玄寂接過信,對比一瞧,點頭道:「這位女施主所說,果然不錯,字跡確實
一摸一樣。」說完,驚疑望向夢中人,剛才夢中人偷襲,已令他生疑。
喬峰向夢中人喝道:「你到底是誰有何居心?」
阿朱忙道:「喬大哥,你且別急,聽我說,玄慈方丈當年讀過這封信,自當
認識信的筆跡,所以這兩封信是慕容興親筆所書無疑,現下關鍵,是要指出那個
慕容興藏在何處,為何不敢露面。」
阿朱說到這裡,又從懷裡拿出來那張撕成兩片的英雄帖,遞給玄寂,然後向
老和尚躬身道:「老法師法眼超凡,當真神僧,小女子阿朱佩服之至。」
老和尚嘆道:「唉!慕容老施主骨相非凡,可惜入了魔道,可惜,可惜!」
玄寂瞧了瞧英雄帖,臉色大變,他此時已對老和尚十分敬服,聽了他與阿朱
這句對話,雖然萬難置信,但心中已無懷疑,當下長身而出。
「石莊主,敢問貴莊所發帖上,「石清敬上」這四個字,是否乃石莊主親筆
所書?這與二十五年前慕容興的筆跡相同,敢問作何解釋?」
眾豪聽到玄慈此問的最後一句,嘩地喧囂起來。
石清的臉色變了幾變,突然大笑幾聲,轉身喊道:「眾位英雄好漢,朝廷腐
敗透頂,無力抵抗外辱,只能欺壓忠義之士。現下的當務之急是抵御官兵,擊潰
官兵後,此間種種,本盟主自會詳明。」
喬峰冷哼一聲,怒視石清,顯然不肯罷休,有些人則又舉刀喊殺起來。
阿朱挺身叫道:「大夥兒慢著,官兵並未攻上山來,依我看,當務之急是請
石莊主解釋,為何眼見玄慈大師自責而死,卻不及時現身,而是隱姓埋名,假傳
消息,如此鬼鬼祟祟,顯見居心叵測,其意不端,如不解釋清楚,眾位好漢怎能
聽你號令。」
千余豪傑頓時又靜默無聲,人中的絕大多數,深以阿朱的話為然。
眾目睽睽下,石清語塞,心裡又驚又怒。
當年,慕容博敗於名劍山莊,一心雪恥,窮盡江湖各派絕學,糅合波斯明教
的「移花接木」心法,創立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但仍然斗不過名劍山莊的
閔嘯天,抑郁而終。
慕容博死後,慕容興假傳武林消息,意圖挑起契丹與大宋的爭斗,以圖趁機
復國,計劃不成,便拋妻離家,隱姓埋名,再尋機會,不想與李夢如結識,真情
迸發,幾乎不能自拔,但為了窺伺名劍山莊武功的秘密,他又拋下李夢如,設計
騙取了閔柔的真情。
幾十年來,化名為石清的慕容興,終於一步步坐到武林盟主之位,從李夢如
的拂塵裡取得當年那封信後,精心布置,引誘喬峰前來與玄慈相斗,準備在收服
少林後,借機聚眾起事,眼見大事將成,一切盡在掌控,沒想到忽然冒出來一個
神秘的老和尚,字跡又洩露了自己的秘密。
總總這一切,其中的辛酸、痛苦,述之不盡,又怎能開口解釋出來!
慕容復奔到石清面前,叫道:「你……你真是我叔父慕容興?」問完,瞧瞧
石清神色,想到石清平日對自己的所說所為,不由又驚又喜,拜倒於地。
石清臉頰抖動,面泛激動,張了張口,似要說什麼,終沒有說出,最後只是
深深嘆了一聲,伸手將慕容復扶起,仰面發出尖細古怪的大笑,如此便即承認了
自己就是慕容興。
群豪震驚之後,哄的沸騰起來,獨石語嫣流著淚,喃喃自語:「你們一起來
騙我,我不信!我不信!」捂面跑走。
段譽失聲叫出:「石姑娘?」再不顧其他,毫不猶豫追趕過去。
此時,石清已知自己半生努力,功敗垂成,不僅作不成武林盟主,亦已不容
於中原豪雄,笑聲如鋼絲直刺天空,聽來無比瘋狂,又無比淒涼。
慕容復眼露驚懼,連連退步。眾人也都收聲驚悚。
喬峰大叫:「奸賊,你膽敢笑什麼?」一掌擊向石清,重傷之中,掌風未及
石清,勢已轉衰。石清笑聲未停,伸掌一轉,引喬峰之力,加上自身內力,忽向
老和尚襲去,心知這個老和尚才是他今日真正的大敵,突然間如推到了一堵無形
氣牆,更似撞進了一張漁網之中。
老和尚依然恍如不知,全不理睬。
石清笑聲頓止,眨眼間退後了好幾丈,伸出食指,憑虛點了三點,他剛才用
出「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運力之秘,這時又使出慕容家的「參合指」,前兩指
點向老和尚,最後一指卻是襲向阿朱。
阿朱對石清毫未提防,她揭發出了一個天大秘密,心裡並不得意,反而有些
難過,她的出身正是姑蘇慕容,雖從未見過慕容興,但論理說,慕容興實是她的
主人,因此正向石清微微躬身,以示謙敬之意。
而虛竹一直睜大眼睛盯著石清,哪敢相信這個自小就無比敬畏的師父,居然
是另外一個人,當初他在曼陀山莊之時,就已聽聞過慕容興之名,由此想到慕容
夫人—那個被他稱之為狐狸精的葉麗絲,心內的驚駭,並不亞於石語嫣,見石清
手指轉向了阿朱,才如夢驚醒,當即擋在阿朱身前,叫聲:「啊喲!」胸口似被
火燒,迷迷糊糊間,只聽老和尚道:「慕容施主,苦海迷航,還不上岸?」
虛竹慢慢睜開雙眼,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布帳頂,跟著發覺自己睡在床上被窩
之中,他只記得自己是遭了暗算,怎麼會睡在一張床上,用力思索,卻無論如何
也想不起,便欲坐起,微一轉動,胸口一陣劇痛,「啊」的叫出來。
外屋的二奴叫道:「主人醒了!」急步進來,後面跟著阿朱,阿朱與虛竹的
目光一觸,止步紅了臉,眼中卻是欣喜笑意。
虛竹歡叫:「阿朱!」眼光不由移到她隆起的小腹上,但覺孕了孩子的阿朱
非但沒有稍減俏麗,更多了幾分慵懶可親的溫婉。
而阿朱嘴角一撇,眼圈紅了,似惱羞成怒,扭身便走。
虛竹一急之下,連連咳嗽,說不出話來。二奴一個給他撫胸,一個給他捶背,
慌得不知怎麼才好,阿朱又回轉來,卻是端來一碗雞湯遞給琴奴。琴奴喂了虛竹
一口,手生膽怯,燙得虛竹直吸涼氣。阿朱不動聲色地從琴奴手裡接過碗,坐到
虛竹面前,伸匙嘴邊,試了試匙羹中的雞湯已不太燙,這才伸到虛竹口邊。虛竹
喝了幾口,覺得舒服多了,擡眼笑眯眯瞧著阿朱。
阿朱放下碗,嗔道:「真是一個色公子!」
虛竹登時心情大暢,但覺這一句親切無比,笑著問起自己如何到了這裡。
阿朱說來,當時石清一擊不中,沒有戀戰,含恨帶著慕容復離去。山上一眾
便做鳥獸散。官兵虛張聲勢喊了幾喊,任由眾豪沖下山,卻有一隊官兵沖上山向
虛竹直奔過來。二奴擡著虛竹,沒了主意,阿朱便領她們逃到了山中這間空屋。
虛竹聽到這裡,心裡知道,那隊官兵必是得了梁從政的命令來保護他,阿朱
不知吉凶,自是帶他逃離,當即心中一熱,暗道:「這妮子對我還是很好。」又
問:「喬大哥呢?」
阿朱道:「喬大哥受傷很重,由那十八個手下保護著,回遼國了,說是再也
不會踏入中原半步。」
虛竹聽了頓生疑惑:「喬峰不會來了?那阿朱怎未跟著離去,她剛才顯出了
委屈之色,難道是二人鬧了別扭?」想到這裡,喜不自禁,咧嘴傻笑。
阿朱稍一尋思,便猜知虛竹所想,扭過頭去滿臉通紅,又瞪一眼道:「每次
都是要死了,還念念不忘亂叫人家!」
虛竹眼睛一亮,握住阿朱的手,笑道:「我昏迷中喚著你了,是不是?」
阿朱臉上又是一紅,輕輕抽出手,似嗔似笑,問道:「哪個是雙兒?」
虛竹一怔,驚道:「我念著雙兒了?」
阿朱沒有應聲,轉目瞧了瞧二奴。
虛竹知阿朱誤會了二奴便是雙兒,一時無從解釋,再去拉她手,不想牽動了
傷處,捂胸忍痛,這才覺知自己確實十分掛念雙兒,不知雙兒和楊三少奶奶現下
在何處?
阿朱皺眉道:「你這傷一時好不了,我知道北冥神功的療傷法,但需要一處
清淨之地,療傷時不得受人打擾,不然反而更是凶險。」
虛竹止住咳嗽道:「我知道山腳有處地方,極為隱蔽。」
過了一會兒,天色暗了,二奴架起虛竹,四人來到山下那間茶棧草屋,經過
一番動亂,到處都空空蕩蕩。
四人進入暗室,阿朱扶著虛竹坐下,自己盤膝坐在他的左側,將北冥神功中
的「療傷篇」背了一遍,講的是若為高手以氣功擊傷,如何以氣功調理真元。
虛竹聽了一遍,便已記住大部,盡管不甚了了,但知若是開始療傷,便不可
中途廢止,否則不僅傷重難治,還要危及性命。當下阿朱伸出右掌,與虛竹左掌
相抵,各自運氣用功,依法練了起來。
二奴從外拿來一個西瓜,阿朱與虛竹分食,兩人手掌卻不分開,從阿朱掌心
傳過來的熱氣緩緩散入虛竹周身百骸,不知不覺過了一夜,不但虛竹胸口的悶塞
舒暢了許多,連阿朱也大感神清氣爽。
此時,一縷晨光從天窗射了進來,照得阿朱白中泛紅的臉,美若朝霞,一雙
小臂露在衣袖之外,皓腕如玉。虛竹與之近在咫尺,越瞧越心蕩。
阿朱見虛竹忽然面紅耳赤,慌張問道:「公子,你怎麼啦?」
虛竹此時氣息紊亂,腦中也迷糊起來,喘著粗氣,不由道:「沒什麼,只是
想抱抱你,親親你。」
阿朱臉上一紅,可無法收掌,也無處去躲,只好羞澀不語,卻更增風致。
虛竹頃刻間情難自制,但覺阿朱的手掌溫軟無比,情欲催動內力紊亂,胸口
開始發漲發痛,哼哼著:「好阿朱,你別生氣,啊啊,我真的好難受!」
阿朱見狀,知道大事不妙,慌道:「我不生氣,但療傷就要成了,千萬不可
動了邪念,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虛竹嗯嗯點頭,臉皮卻瞬間漲得血紅。
「公子,你回蝴蝶谷找過我,是不是?」
阿朱急中生智,突然問了一句,只想叫虛竹不要再胡思亂想。
虛竹點點頭。
阿朱急忙接著說下去,當日虛竹離開蝴蝶谷不久,丁春秋闖入谷來,將阿朱
和蘇星河擄走,小蝶向爹爹撒嬌耍潑,護著阿朱和蘇星河,丁春秋無奈何,且見
愛女腿傷未愈,只好不敢為難二人。一日,小蝶與李夢如相斗,突然出現怪異的
白發女子。
虛竹聽到這裡,氣息已平,笑道:「好阿朱,你不知,那時我也在。」便將
那日之事說了,再道:「我好生後悔,當時沒能及時認出你來。」
阿朱開懷笑道:「是啊,我也想不到,即便想到你易了容,也絕不會想到你
居然扮得比平日更醜,我帶喬大哥去救出了蘇前輩,但小蝶又中了毒針,我只得
再去……」說到這裡,阿朱忽然十分羞澀,又紅了臉,低首不語。
虛竹等了片刻,奇怪道:「李夢如那麼凶狠,你如何奪的解藥?」
阿朱不答,臉上羞紅未褪,又罩上了一層薄暈。
虛竹察覺到阿朱的氣息突然變得紛亂,吃驚喚道:「阿朱!」
阿朱急忙鎮懾心神,伸直手臂,支吾道:「再有一時半刻,就該好了,咱們
不要說話,用心運功。」
虛竹更加奇怪,專心運功後,手掌中隱隱感覺到阿朱內息中潛在的胎動,心
道:「不管如何,只要是俏阿朱的,我一概全收,以後不許她離身半步,即大功
告成。」
虛竹在後追那老和尚,見他手提二屍,邁開大步,東一轉,西一拐,如淩虛
而行,直往寺後而去。虛竹加快腳步,奮力急奔,眼見距那老和尚的背後只有了
兩三丈之遙,卻無論如何也追趕不上。
到了林間一處平曠之地,老和尚將兩具屍身放在一株樹下,將其都擺成盤膝
而坐的姿勢,他坐去二屍後,雙掌分別抵住兩個身背。
虛竹趕到時,老和尚似在自語:「奔走一程,他們的血脈也該活動了。」
虛竹心下一凜:「哪有將人打死再救活之理?」
接著,二奴氣籲籲趕來,立在主人身後。
老和尚開始擺掌在屍身上不住拍擊,二屍頭頂之上忽然冒出縷縷白氣,越來
越濃,過了一盞茶時分,兩個屍身同時微微顫動,慢慢睜開眼來。
虛竹驚奇之極,能夠叫心不跳而人又不死,實是聞所未聞。
老和尚站去丁春秋和蘇星河面前,問道:「你們可還有什麼放不下?」
丁春秋和蘇星河互視一眼,一齊向老和尚跪下,神情與之前大不一樣。
虛竹更加驚奇,卻不知此二人已由生到死、由死到生地走了一回,雖然只有
短短時間,但其中種種經歷感覺,凡人只有死後才能得以體驗,其情其狀,實非
世間言語所能描述。
蘇星河道:「弟子號稱神醫,一生救治過不少人,也有許多見死不救,有時
洋洋得意,有時暗暗內疚。現下看來,救與不救,醫與不醫,皆世間空幻,唯有
佛門慧根方能得識,弟子懇請師父收錄。」
老和尚微微點頭,轉向蹙眉沈思的丁春秋,笑道:「歷經一生一死,生死符
即已無用,施主現下去哪裡,這就請便吧。」
丁春秋似乎一驚,面露迷惘。
「我……我武功已失,生平殺人百數,死後那些人皆來復仇索命,我實不知
能逃到哪裡去?求師父收為弟子,救我跳出火坑。」
老和尚哈哈笑道:「善哉,善哉!佛門隨緣而度,你們想要為僧,須求寺中
的大師們剃度。」說罷,從虛竹手裡輕輕拿過掃帚,似乎隨意道:「你們且隨我
掃地去吧。」
丁春秋和蘇星河都是一愣,但知老和尚的話必大有深意。
虛竹當然亦不知其意,但此時對老和尚欽佩之至,不敢出聲,帶著二奴悄悄
隨在老和尚的身後,心想:「他只輕輕一掌便可將人收服,叫丁春秋這等惡人也
死心塌地,比生死符還要厲害十倍,不知他肯不肯教我,我去拍一拍阿朱,順手
也拍一下那個紅發妖女,叫她們兩個都哭著求我收留,最好不過!」
幾人回到寺前,遠遠見到人群後,老和尚將掃帚遞給丁春秋。
「你去吧。」
丁春秋躬身接過掃帚,雖有所悟,可無法像老和尚那樣旁若無人得在人群中
掃來掃去,而是躲去僻靜處,藏頭掃起。
老和尚向蘇星河道:「你也去吧。」
蘇星河面露疑惑,攤開雙手,意即沒有掃帚。
老和尚微笑道:「掃地即掃心,當下便是掃帚,我已給了你,還不快去!」
蘇星河一怔之後,歡欣鼓舞而去,伏到青石路上將落葉一葉一葉拾起,專心
致志,毫無旁騖。
此刻,虛竹已穿過人群,即大吃一驚,見喬峰跪在玄慈身前,衣上、頭上、
臉上,到處都是唾沫痰漬,醃臢不堪,慘不忍睹,幾乎瞧不清面目。
「大哥?」
虛竹吃驚叫了聲,快步到喬峰身旁,不知他因何而此。
段譽也從人中穿出,喜叫道:「三弟,你安然無事,真是太好了。」然後向
眾人道:「現下我大哥需要療傷,再有哪位英雄想要洩憤,向我唾來好了。」
段譽向來好潔,說出此話,實是下了好大決心,語意甚誠。
喬峰站起,向一名契丹武士要過酒囊,打開囊塞,舉在頭頂,用酒水淋去了
頭臉上的汙漬,然後仰頭喝了一口,隨即撲哧一聲,連血帶酒噴了出來,他受傷
甚重,這口酒居然壓不下,便將酒囊一扔,捂著胸口道:「謝二弟、三弟,現今
大哥已無牽掛,唯有銘記兄弟之間的恩情!」說到這裡,哈哈一笑,向眾人朗聲
道:「我喬峰今日過後,與江湖再無恩怨,也再不踏入中原半步。現下哪位仍覺
不解恨,盡管出來比劃,喬峰自當奉陪。」
肅靜了好一會兒,終有一人走了出來,瞧著他們兄弟三人,遲疑著不敢冒險
一試,自知絕不是對手,只好滿面羞慚退了回去。
這時,一夥人從山下跑來,慌張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官兵來了,堵著
路口,密密麻麻,也不知來了多少。」
眾豪登時紛亂起來,有人叫道:「大家慌什麼,官兵向來是虛張聲勢,我們
不走大路,四散沖出,他們自拿我們沒有辦法。」
石清慢慢走出人群,眾豪一見,漸漸噤聲。石清站定,皺眉道:「這位兄弟
說的不錯,但官兵明知我武林大會,仍來肆意挑釁,欺各位英雄太甚,我們一再
示弱,官府以後更要猖狂無比。」
當即有人呼應道:「石盟主說的不錯,我們人人以一當十,再多的官兵也殺
他個屁滾尿流,叫朝廷再不敢小覷我們。」
此語一出,越來越多的人舉起了兵器,揮舞叫嚷。
玄寂走出道:「阿彌陀佛!現下情況不明,絕不可擅起干戈。」
石清轉向玄寂道:「大師說的是,請布下少林羅漢陣,保護我等下山。」
玄寂吃驚道:「這個……少林寺乃方外之地,濟世之所,自始以來從不輕易
與朝廷為敵。」
石清微微一笑,大聲道:「保護在場眾位英雄的身家性命,總不會是違背了
我佛降妖伏魔的本義了吧?」
玄寂一時無言以對,眾豪也頃刻消聲,靜候玄寂表態。
忽然清楚傳來一聲:「唉!慕容施主,你目睹他們兩個互相搏斗,怎不出來
解釋清楚?」
眾人望去,說話的是那個掃地的老和尚,正看著玄慈的屍身不住搖頭。眾人
目光紛紛轉向慕容復,此際除了他,場中再無慕容氏。
慕容復因自己「春光曝現」,躲在角落仍羞慚不已,見眾人望來,登時滿臉
通紅,不得已道:「他們之間三十多年前的恩怨,我怎能解釋清楚?」眾人一聽
皆覺如此,三十多年前,慕容復大概還未出生,怎會牽涉此事?
老和尚擡起茫然無神的眼珠,目光沿著圍成一圈的人群向慕容復尋去。眾人
見他目光遲鈍,直如視而不見其物,卻又似自己心中所藏的秘密,每一件都被他
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心中發毛,周身大不自在。
老和尚將目光轉到慕容復臉上,只停了一停,便佝僂下身子緩行幾步,面向
石清道:「老衲已記不清那是多少年前,那時,玄慈方丈剛入我佛門,他與你在
藏經閣前會面,說了一些事,慕容施主可否記得?」
石清沈默片刻,不動聲色道:「在下不知法師說些什麼?」
老和尚搖搖頭,嘆道:「是啊,時間有些久了,當時你們都蒙著面,但老衲
識人,不記其面,只記其骨。人的一生,骨相要比面相可靠多了,因此老衲通常
不會認錯,你們一個自稱路雲天,另一個自稱慕容興。」
眾人哄得議論紛紛,路雲天,一代大俠,當年名震天下,而慕容興在慕容博
隱退後,成為姑蘇慕容的年輕掌門人,二人當時的名頭就如當今的「北喬峰、南
慕容」一般,但二人突然同時銷聲匿跡,成為江湖中的一件懸案。今日卻從一個
看似瘋癲呆傻的老和尚口中說出,且指名道姓,豈不駭人聽聞?
石清又沈默一會兒,冷笑一聲,向玄寂道:「大師,在下對荒謬的道聽途說
並不關心。現下官兵圍攻,江湖形勢危急,少林顧及自保,不願出手相助,也是
情有可緣,但請約束屬僧,不要擾亂視聽!」
石清說到最後,聲音發顫,顯然已經發怒。
人群中,忽然又傳來一聲:「依我看,擾亂視聽的,實是另有其人!」
阿朱走出人圈,手裡舉起那兩封書信,接著說道:「這裡有兩份書信,一封
是三十年前慕容興所書,另一封是近日寫給喬大哥的匿名書信,大家看,這兩份
書信的筆跡完全相同,難道是慕容興陰魂不散,給喬大哥寫了這封信?」
阿朱說著向喬峰走去,人影一閃,夢中人向她搶去。喬峰瞧得清楚,忙出掌
攔阻,剛一發力,便咳出一口血來,而他身旁的虛竹和段譽,機靈不足,待發覺
不妙時,夢中人已經到了阿朱身後。
阿朱練了北冥神功的療傷篇,不僅治好了內傷,應機也大勝從前,感到身後
傳來異風,頭也不回,向後擺手發力,趁勢踏出淩波微步,隨即捂著小腹,不由
一個趔趄,她懷有身孕,猛一催動真氣,小腹便是一痛,吃驚回頭,見夢中人在
身後高舉著一只手臂,身子前傾卻動彈不得,好似被什麼無形之物阻住,手指裡
捏著一根熠熠閃光的細針。
這時,虛竹的天山六陽掌和喬峰的降龍十八掌,都已發向夢中人的後心。
那老和尚站在幾丈遠處,原本已伸出一只手,此時將雙臂合抱,便似推出了
一堵無形高牆,擋在夢中人身後。天山六陽掌和降龍十八掌撞在這堵牆上,登時
無影無蹤,同時消於無形。
喬峰咳嗽著驚異之至。玄寂默念阿彌陀佛,心想這般潛運神功,先是定住了
夢中人的詭異身法,再又阻住了喬峰二人那排山倒海的掌力,莫非這位自己從未
留意的老僧,竟是菩薩化身,否則怎有如此神通?
老和尚收回雙手,緩緩合什,誦道:「陳彌陀佛,佛門善地,眾位施主不可
妄動無明。」
夢中人嗖地退回原處,她這一進一退,都是無影無聲。阿朱瞧得害怕,忙走
幾步,躲到老和尚身後,向玄寂遞過那兩封信。
玄寂接過信,對比一瞧,點頭道:「這位女施主所說,果然不錯,字跡確實
一摸一樣。」說完,驚疑望向夢中人,剛才夢中人偷襲,已令他生疑。
喬峰向夢中人喝道:「你到底是誰有何居心?」
阿朱忙道:「喬大哥,你且別急,聽我說,玄慈方丈當年讀過這封信,自當
認識信的筆跡,所以這兩封信是慕容興親筆所書無疑,現下關鍵,是要指出那個
慕容興藏在何處,為何不敢露面。」
阿朱說到這裡,又從懷裡拿出來那張撕成兩片的英雄帖,遞給玄寂,然後向
老和尚躬身道:「老法師法眼超凡,當真神僧,小女子阿朱佩服之至。」
老和尚嘆道:「唉!慕容老施主骨相非凡,可惜入了魔道,可惜,可惜!」
玄寂瞧了瞧英雄帖,臉色大變,他此時已對老和尚十分敬服,聽了他與阿朱
這句對話,雖然萬難置信,但心中已無懷疑,當下長身而出。
「石莊主,敢問貴莊所發帖上,「石清敬上」這四個字,是否乃石莊主親筆
所書?這與二十五年前慕容興的筆跡相同,敢問作何解釋?」
眾豪聽到玄慈此問的最後一句,嘩地喧囂起來。
石清的臉色變了幾變,突然大笑幾聲,轉身喊道:「眾位英雄好漢,朝廷腐
敗透頂,無力抵抗外辱,只能欺壓忠義之士。現下的當務之急是抵御官兵,擊潰
官兵後,此間種種,本盟主自會詳明。」
喬峰冷哼一聲,怒視石清,顯然不肯罷休,有些人則又舉刀喊殺起來。
阿朱挺身叫道:「大夥兒慢著,官兵並未攻上山來,依我看,當務之急是請
石莊主解釋,為何眼見玄慈大師自責而死,卻不及時現身,而是隱姓埋名,假傳
消息,如此鬼鬼祟祟,顯見居心叵測,其意不端,如不解釋清楚,眾位好漢怎能
聽你號令。」
千余豪傑頓時又靜默無聲,人中的絕大多數,深以阿朱的話為然。
眾目睽睽下,石清語塞,心裡又驚又怒。
當年,慕容博敗於名劍山莊,一心雪恥,窮盡江湖各派絕學,糅合波斯明教
的「移花接木」心法,創立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但仍然斗不過名劍山莊的
閔嘯天,抑郁而終。
慕容博死後,慕容興假傳武林消息,意圖挑起契丹與大宋的爭斗,以圖趁機
復國,計劃不成,便拋妻離家,隱姓埋名,再尋機會,不想與李夢如結識,真情
迸發,幾乎不能自拔,但為了窺伺名劍山莊武功的秘密,他又拋下李夢如,設計
騙取了閔柔的真情。
幾十年來,化名為石清的慕容興,終於一步步坐到武林盟主之位,從李夢如
的拂塵裡取得當年那封信後,精心布置,引誘喬峰前來與玄慈相斗,準備在收服
少林後,借機聚眾起事,眼見大事將成,一切盡在掌控,沒想到忽然冒出來一個
神秘的老和尚,字跡又洩露了自己的秘密。
總總這一切,其中的辛酸、痛苦,述之不盡,又怎能開口解釋出來!
慕容復奔到石清面前,叫道:「你……你真是我叔父慕容興?」問完,瞧瞧
石清神色,想到石清平日對自己的所說所為,不由又驚又喜,拜倒於地。
石清臉頰抖動,面泛激動,張了張口,似要說什麼,終沒有說出,最後只是
深深嘆了一聲,伸手將慕容復扶起,仰面發出尖細古怪的大笑,如此便即承認了
自己就是慕容興。
群豪震驚之後,哄的沸騰起來,獨石語嫣流著淚,喃喃自語:「你們一起來
騙我,我不信!我不信!」捂面跑走。
段譽失聲叫出:「石姑娘?」再不顧其他,毫不猶豫追趕過去。
此時,石清已知自己半生努力,功敗垂成,不僅作不成武林盟主,亦已不容
於中原豪雄,笑聲如鋼絲直刺天空,聽來無比瘋狂,又無比淒涼。
慕容復眼露驚懼,連連退步。眾人也都收聲驚悚。
喬峰大叫:「奸賊,你膽敢笑什麼?」一掌擊向石清,重傷之中,掌風未及
石清,勢已轉衰。石清笑聲未停,伸掌一轉,引喬峰之力,加上自身內力,忽向
老和尚襲去,心知這個老和尚才是他今日真正的大敵,突然間如推到了一堵無形
氣牆,更似撞進了一張漁網之中。
老和尚依然恍如不知,全不理睬。
石清笑聲頓止,眨眼間退後了好幾丈,伸出食指,憑虛點了三點,他剛才用
出「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運力之秘,這時又使出慕容家的「參合指」,前兩指
點向老和尚,最後一指卻是襲向阿朱。
阿朱對石清毫未提防,她揭發出了一個天大秘密,心裡並不得意,反而有些
難過,她的出身正是姑蘇慕容,雖從未見過慕容興,但論理說,慕容興實是她的
主人,因此正向石清微微躬身,以示謙敬之意。
而虛竹一直睜大眼睛盯著石清,哪敢相信這個自小就無比敬畏的師父,居然
是另外一個人,當初他在曼陀山莊之時,就已聽聞過慕容興之名,由此想到慕容
夫人—那個被他稱之為狐狸精的葉麗絲,心內的驚駭,並不亞於石語嫣,見石清
手指轉向了阿朱,才如夢驚醒,當即擋在阿朱身前,叫聲:「啊喲!」胸口似被
火燒,迷迷糊糊間,只聽老和尚道:「慕容施主,苦海迷航,還不上岸?」
虛竹慢慢睜開雙眼,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布帳頂,跟著發覺自己睡在床上被窩
之中,他只記得自己是遭了暗算,怎麼會睡在一張床上,用力思索,卻無論如何
也想不起,便欲坐起,微一轉動,胸口一陣劇痛,「啊」的叫出來。
外屋的二奴叫道:「主人醒了!」急步進來,後面跟著阿朱,阿朱與虛竹的
目光一觸,止步紅了臉,眼中卻是欣喜笑意。
虛竹歡叫:「阿朱!」眼光不由移到她隆起的小腹上,但覺孕了孩子的阿朱
非但沒有稍減俏麗,更多了幾分慵懶可親的溫婉。
而阿朱嘴角一撇,眼圈紅了,似惱羞成怒,扭身便走。
虛竹一急之下,連連咳嗽,說不出話來。二奴一個給他撫胸,一個給他捶背,
慌得不知怎麼才好,阿朱又回轉來,卻是端來一碗雞湯遞給琴奴。琴奴喂了虛竹
一口,手生膽怯,燙得虛竹直吸涼氣。阿朱不動聲色地從琴奴手裡接過碗,坐到
虛竹面前,伸匙嘴邊,試了試匙羹中的雞湯已不太燙,這才伸到虛竹口邊。虛竹
喝了幾口,覺得舒服多了,擡眼笑眯眯瞧著阿朱。
阿朱放下碗,嗔道:「真是一個色公子!」
虛竹登時心情大暢,但覺這一句親切無比,笑著問起自己如何到了這裡。
阿朱說來,當時石清一擊不中,沒有戀戰,含恨帶著慕容復離去。山上一眾
便做鳥獸散。官兵虛張聲勢喊了幾喊,任由眾豪沖下山,卻有一隊官兵沖上山向
虛竹直奔過來。二奴擡著虛竹,沒了主意,阿朱便領她們逃到了山中這間空屋。
虛竹聽到這裡,心裡知道,那隊官兵必是得了梁從政的命令來保護他,阿朱
不知吉凶,自是帶他逃離,當即心中一熱,暗道:「這妮子對我還是很好。」又
問:「喬大哥呢?」
阿朱道:「喬大哥受傷很重,由那十八個手下保護著,回遼國了,說是再也
不會踏入中原半步。」
虛竹聽了頓生疑惑:「喬峰不會來了?那阿朱怎未跟著離去,她剛才顯出了
委屈之色,難道是二人鬧了別扭?」想到這裡,喜不自禁,咧嘴傻笑。
阿朱稍一尋思,便猜知虛竹所想,扭過頭去滿臉通紅,又瞪一眼道:「每次
都是要死了,還念念不忘亂叫人家!」
虛竹眼睛一亮,握住阿朱的手,笑道:「我昏迷中喚著你了,是不是?」
阿朱臉上又是一紅,輕輕抽出手,似嗔似笑,問道:「哪個是雙兒?」
虛竹一怔,驚道:「我念著雙兒了?」
阿朱沒有應聲,轉目瞧了瞧二奴。
虛竹知阿朱誤會了二奴便是雙兒,一時無從解釋,再去拉她手,不想牽動了
傷處,捂胸忍痛,這才覺知自己確實十分掛念雙兒,不知雙兒和楊三少奶奶現下
在何處?
阿朱皺眉道:「你這傷一時好不了,我知道北冥神功的療傷法,但需要一處
清淨之地,療傷時不得受人打擾,不然反而更是凶險。」
虛竹止住咳嗽道:「我知道山腳有處地方,極為隱蔽。」
過了一會兒,天色暗了,二奴架起虛竹,四人來到山下那間茶棧草屋,經過
一番動亂,到處都空空蕩蕩。
四人進入暗室,阿朱扶著虛竹坐下,自己盤膝坐在他的左側,將北冥神功中
的「療傷篇」背了一遍,講的是若為高手以氣功擊傷,如何以氣功調理真元。
虛竹聽了一遍,便已記住大部,盡管不甚了了,但知若是開始療傷,便不可
中途廢止,否則不僅傷重難治,還要危及性命。當下阿朱伸出右掌,與虛竹左掌
相抵,各自運氣用功,依法練了起來。
二奴從外拿來一個西瓜,阿朱與虛竹分食,兩人手掌卻不分開,從阿朱掌心
傳過來的熱氣緩緩散入虛竹周身百骸,不知不覺過了一夜,不但虛竹胸口的悶塞
舒暢了許多,連阿朱也大感神清氣爽。
此時,一縷晨光從天窗射了進來,照得阿朱白中泛紅的臉,美若朝霞,一雙
小臂露在衣袖之外,皓腕如玉。虛竹與之近在咫尺,越瞧越心蕩。
阿朱見虛竹忽然面紅耳赤,慌張問道:「公子,你怎麼啦?」
虛竹此時氣息紊亂,腦中也迷糊起來,喘著粗氣,不由道:「沒什麼,只是
想抱抱你,親親你。」
阿朱臉上一紅,可無法收掌,也無處去躲,只好羞澀不語,卻更增風致。
虛竹頃刻間情難自制,但覺阿朱的手掌溫軟無比,情欲催動內力紊亂,胸口
開始發漲發痛,哼哼著:「好阿朱,你別生氣,啊啊,我真的好難受!」
阿朱見狀,知道大事不妙,慌道:「我不生氣,但療傷就要成了,千萬不可
動了邪念,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虛竹嗯嗯點頭,臉皮卻瞬間漲得血紅。
「公子,你回蝴蝶谷找過我,是不是?」
阿朱急中生智,突然問了一句,只想叫虛竹不要再胡思亂想。
虛竹點點頭。
阿朱急忙接著說下去,當日虛竹離開蝴蝶谷不久,丁春秋闖入谷來,將阿朱
和蘇星河擄走,小蝶向爹爹撒嬌耍潑,護著阿朱和蘇星河,丁春秋無奈何,且見
愛女腿傷未愈,只好不敢為難二人。一日,小蝶與李夢如相斗,突然出現怪異的
白發女子。
虛竹聽到這裡,氣息已平,笑道:「好阿朱,你不知,那時我也在。」便將
那日之事說了,再道:「我好生後悔,當時沒能及時認出你來。」
阿朱開懷笑道:「是啊,我也想不到,即便想到你易了容,也絕不會想到你
居然扮得比平日更醜,我帶喬大哥去救出了蘇前輩,但小蝶又中了毒針,我只得
再去……」說到這裡,阿朱忽然十分羞澀,又紅了臉,低首不語。
虛竹等了片刻,奇怪道:「李夢如那麼凶狠,你如何奪的解藥?」
阿朱不答,臉上羞紅未褪,又罩上了一層薄暈。
虛竹察覺到阿朱的氣息突然變得紛亂,吃驚喚道:「阿朱!」
阿朱急忙鎮懾心神,伸直手臂,支吾道:「再有一時半刻,就該好了,咱們
不要說話,用心運功。」
虛竹更加奇怪,專心運功後,手掌中隱隱感覺到阿朱內息中潛在的胎動,心
道:「不管如何,只要是俏阿朱的,我一概全收,以後不許她離身半步,即大功
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