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友站 番號最齊 新作上架最快!(每天更新百部AV)
請使用轉址到網站新介面模板瀏覽, 10 秒后,
会转跳到 ==> https://18av.mm-cg.com
小說名稱:[經驗故事]通行證之誘惑
文字放大: 自訂文字大小: 行距:|
看著腳下那一條條長長的麥垅,周舟直想哭。一條麥垅的長度是一千米,她每拔一把麥子的長度是三十多公分,她計算著,拔完一垅麥子需要她彎腰費力地拔三千多次。此時已近晌午,她還沒拔完一條麥垅的一半,而今天分配下來的,要她拔完的麥子有六垅。只好直著快要直不起來的腰,收回僵硬得像是快要斷掉的胳膊,無奈地望著,早晨一塊兒從地頭出發,現在卻離她越來越遠的人群。 太陽火辣辣的,沒有一絲風。周舟的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她不停地擦著臉上和脖頸間的汗水。她真想學同屋小雲的樣子,用菜刀把自己的手切了,切得厲害些,那樣她就能有法子不出工,蹭過這個麥收。她想著,伸出雙手看著,切哪只手好呢?真受不了! 「周舟。」有人在喊她。她轉過身看去,見生產隊長大馬站在樹下,招呼著她。 「找我有事?」周舟走過去,能伸直腰的感覺真好,隨意地邁著腿,甩甩酸疼的胳膊,得警惕點,這大馬不是好人,他琢磨什麼呢? 「也沒啥要緊事兒,」大馬示意她坐下,「歇會兒吧。」 樹陰下涼快多了,周舟摘下草帽,拿在手裡扇著。別坐下,那樣會有助他動手動腳。她想起前天在井邊,就是因為沒防備,讓他摸了個正著。 「也沒啥要緊事兒。」大馬掏出香煙,悠然地點上,抽,什麼事情讓他這麼胸有成竹的?周舟覺得一陣緊張,但表面必須鎮定。「早上公社來了電話,打聽咱們這兒有沒有個叫周舟的?」 「打聽我!」周舟驚詫地問,「打聽我幹嘛?」 大馬沒言語。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周舟又問。 「我聽說,是城裡大學來招生的人打聽你來著。」大馬說著,又揮了下手,「你就坐在這兒,怕啥?」 聽到這個消息,周舟不由喜形於色。會是誰呢?她最先想到的就是一直輔導自己外語的張伯伯,對,肯定是他。剛才在麥地裡她那種沮喪的心情,此刻,已經被突如其來的喜悅所代替。她覺得心底中有股希望的火苗,忽忽地、悠悠地燃燒起來。也許,應該先坐下來,他大概還沒有說完。 周舟坐下,靠在樹幹上,瞇著眼睛看遠處,草帽不停地扇著,她的前胸、後背,很快感到微風的吹拂。她能感覺出大馬的目光正在不失時機地利用她襯衫領口處被風撩起的那一剎,準確地落在她的胸脯上。 你要是能上大學該多好啊!她的耳邊迴響起張伯伯的話,迄今為止,她還沒有到過任何一所大學校園,她只能憑藉著想像,勾畫著大學的模樣。優美、靜謐的校園,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的教授們,豐富多采的、充滿浪漫故事的大學學生生活……大馬那只伸向她胸脯的手打斷了她的遐想。 「馬隊長,」周舟平靜地叫了一聲,依舊坐在那裡,沒動。那隻手停在了空中。 「您要是沒別的事,我還得拔麥子去呢。」周舟站起身,「我還剩好幾垅沒拔呢。」 「別,先別忙著走。」大馬那停在半空的手找到了用處,他一把拉住周舟的衣角,「那點麥子算啥,回頭我讓別人給你拔了,我話還沒說完呢……」 又是好消息。「公社電話裡還說,他們的人要下來看看你。」大馬猥褻地瞟了周舟一眼,得意地,「你也知道,這年頭讓誰上大學,不讓誰上大學,還不是咱們貧下中農說了算!」 「那當然了,」周舟順口搭音地恭維著,「您要是不想讓誰上大學,誰來了也是白搭。」 「對,對,你真精!我早就說過了,咱們隊上這幫知青,就數周舟最精。」大馬又點上一支煙,「我這個還是從來都不計較出身,你說出身那玩意算個啥?那不是扯淡麼?我這個就看表現,就看重個人表現怎麼樣?總不能接受了幾年貧下中農再教育,一點表現都沒有,就想走啊?更甭提上大學這樣的美事兒了!」赤裸裸的威脅。 天啊!怎麼盡碰上這樣的人?王八蛋!儘管周舟早就下定決心不再罵人,但此刻,她又在心裡罵起來了。 怎麼辦?她此刻腦海裡又一次浮出她無數次勾畫出的那所外語學院的模樣,她無法控製自己。 這陣子,她走火入魔地想上大學,眼下,機會來了,逃離苦海,步入大學的道路就在這兒明擺著,你還猶豫什麼?趕快上路吧。她那懵懂雜亂的耳際,彷彿有一個聲音雜催促著她。 「馬隊長,」她和顏悅色地,「人家說哪會兒到咱們隊上來了嗎?」 「說是今天就來。」大馬又往周舟的身邊湊了湊,鼻子抽動了幾下,「其實招生表早就在手裡……我還沒拿準給誰呢。」 他能決定別人的命運,他權利真大,魔鬼儘是有權的! 周舟側著身子站著,她感到大馬那粗重的喘息離她越來越近,一股連蔥帶蒜的口臭撲面而來。她厭惡地皺了下眉,使勁扇著手裡的草帽。 現在,能夠看到的大學之路就在眼前,不幸的是,這路上有魔鬼把守。別抱怨自己命運不濟,因為你趕上了這樣一個魔鬼輩出的時代。向你索取的是這樣的通行證--你的身體。 假若,非要選擇一下,你怎麼選擇?去他媽的!她在心裡罵著。 那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離她更近了,她咬緊嘴唇,硬挺著。也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對她個人而言,應該包括即將進行的課程?她不再繼續往下想了。突然她想起身就走,離開那惡臭,但片刻間就打消了念頭。她感到她的大腿被按住了,緊接著,乳房上又摸上來一隻手。 「馬隊長,你這是幹嘛……」她尖細地驚叫著,站起來,閃躲到一旁。那惶恐出色的神情,與貞操受到威脅的純潔少女並無二樣,她具有潛在的表演才能,有即興出色發揮的基因,她身體顫抖,面色羞紅,站在那裡像一隻受到驚嚇的小綿羊。 「你怕啥?」大馬四處望著,也站起身,「咋地啦……你剛才不是說,想上大學嗎?」他急了,先將底牌亮了出來。 「你真的能讓我上大學?」周舟問著,抬起頭,那對水靈靈的眸子裡閃爍著驚喜、期冀的光芒。 「不信是咋的?這地方,我說了算!」大馬見四下無人,膽又大了起來,他拉著周舟的手,揉搓著。「這手長的多白嫩,幹這傻莊稼活兒都糟蹋了。怪不得老娘們兒都說,滿村兒裡就數你長的俊!」 「馬隊長,別這樣……」周舟扭捏地掙脫他的手,「讓人看見多不好。」 大馬無可奈何地站在那兒,喘著粗氣。看得出來,他已經急不可耐了。 「我這就回村兒,讓孩子他媽帶著孩子回娘家住去。」他色瞇瞇地盯著周舟,急切地說。 「您別,您可別這樣……」周舟拽下了大馬的胳膊,「我現在就想看那張招生表。」她說著,看到公路下,一輛吉普車正向村兒裡疾駛而去。 院門是開著的,周舟推開門,走進去,院子裡沒有人。周舟叫了一聲,沒有回音。她走向北屋,撲面而來的那股味跟大馬身上的那股味一樣,她沒走錯門。 屋裡很髒,比她想像的還要髒一些。北窗下是一溜土炕,南面是用磚頭和水泥砌起來的一溜地櫃。她估計,這個家連同糧食在內的全部家當,肯定都在這櫃子裡。牆上有幾隻鏡框,裡面裝著獎狀和一些發黃的照片。周舟辨認出來,那中間有一張是年輕時的大馬,他穿著軍裝,肩上扛著少尉軍銜。土炕一頭摞著幾條被子,髒兮兮的,呆會兒可別用它。 一天來,事情進行的很順利。她和外語學院的人見了面,從他們的言談中能聽出她已經面試過關了。招生表也拿到並且填上了部分內容,當然,表格中推薦評語一欄還空著,最為關鍵的公章也還沒有蓋上。這一切都要取決於她今晚的表現。雙方已經達成默契,現在只剩下履行約定了。 周舟掃了一眼這鋪著一領破席的土炕,這重要的事兒,呆會兒就得在這上面辦。她感到噁心,乾嘔了幾聲,卻沒吐出來。 「你咋的啦?」大馬撩開門簾走進屋。 屋裡的氣味兒實在難忍,她又感到一陣噁心。堅持住,別太煞風景,這魔鬼已經部分地兌現了承諾,他也應該有所表現。是不是反守為攻?可以縮短一下這個過程麼?她有些後悔,早知道如此,還不如上午就在空氣新鮮的田間地頭把事兒干了。 大馬的頭髮濕漉漉的,臂膀上還帶著水珠兒,看樣子像是剛沖了個澡。他走到地櫃前,對著掛在牆上的一塊破鏡子,擼著頭。周舟看到鏡子旁邊有一瓶還沒啟封的白酒。 「來招生的人都走了嗎?」他問。 「走了。」她答。 「晚飯是你陪他們一塊兒吃的?」 「是。」 「你們一塊兒談的不錯吧?」 周舟沒說話。 「我看那幾個人是看上你了……其實,跟他們談是瞎掰,沒有基層的推薦,誰來我也能給頂回去。」 「我知道……」周舟低著頭,輕聲細語地,「現在不就是來找您麼。」 「這就對了!舟舟……」大馬湊過來,坐在炕沿上,攬住她的腰。她感到全身一陣發冷,手腳變得冰涼。 「別害怕。」 他摸著她的臉頰。「我這個人吶,沒別的嗜好,就是喜歡個俊俏閨女兒,要不是為這事背了個處分,我現在怎麼也弄得個師長干干了。」 壞事!碰上個老手。周舟一驚,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怎麼辦?剛才她還想反守為攻的自信遭到了當頭一棒。 「馬隊長,」周舟抬起燒得嫣紅的臉龐,指著地櫃上的那瓶酒,「那是酒嗎?」 「是呀,咋啦?」 「我想喝點兒。」 「喝吧,人家送的,也想上大學……」大馬鬆開了周舟,走過去,將酒瓶打開,遞給她。「你能喝白酒?」 她點了點頭,接過酒瓶,喝了一口。 別害怕,周舟,堅持住,周舟。這裡也是戰場,這裡就是你與命運抗爭的戰場,不要嫌身下這鋪上骯髒,這裡能通向高等學府的殿堂,不要嫌這個魔鬼貪婪、醜陋,他在嘗到你的鮮肉之後,起碼能付給你夢寐以求的東西。 開始吧,你還等什麼?再喝一口。好了,酒精在起作用了,這事兒不會有人知道的,你已經無路可走了,來吧,魔鬼。 周舟神情恍惚地轉過身,放下酒瓶,臉上顯露著服從的神情,她感到好一陣緊張--但絕不是害怕--從心底油然而升。 他開始親她,她閉上眼睛,順從地承受著。他把她推倒在炕上,迅速地扒光她的衣服。月光從窗外射進來,照在她雪白、豐腴的裸體上,他手忙腳亂、氣喘籲籲地揉搓她。 序幕剛剛拉開,她就感到,今天晚上不會輕易地放她走的,她緊張地等待著他的插入。揉搓越來越劇烈,他用他那粗糙的雙手用力地揉搓著眼前這具細嫩而又極其富有彈性的身體,他發狠似的又擰又捏,突然,他伏下身,在她的屁股上咬了一口。 「哎喲!」她尖叫了一聲,睜開眼睛。只見他氣喘籲籲,大汗淋漓,那目光如同夜中的狼,冒著綠光。 「他媽的!怎麼不行了……」他低頭捏著他腰間那個東西,懊喪地罵,「你他媽的還不快給我起來,快起來!」 她噌地一下坐起來,跳到地下。 「沒說你!」他氣急敗壞地嚷著,「你他媽的快給我上來,老老實實地躺在這兒!」 她嚇壞了!她怎麼也沒有料到會發生這一幕,她驚慌失措地站在地下,嚇得大氣也不敢出。要壞事,照這麼下去,他說的話還算不算數? 「你聾啦,快他媽的上來。」他嚷著,自己平躺在炕上。 她顫抖著爬上炕,躺在他的身旁。 「你起來。」他拽過她的手,放在他的陰莖上,「你給我弄弄。」 她的頭髮披散著,跪在他的身旁,她用雙手摀住眼睛,不敢看他一眼。 「你他媽的快弄啊!」他急了,一巴掌打在她的腿上。 怎麼弄?是不是象拔麥子一樣?她握著那軟塌塌的陰莖,不知怎麼才好。 「你輕點兒。」他又嚷起來了。 她迅速地調整一下手勢和力度。 「再使勁一點。」他仍不滿意。她只得再做調整。 他的手從旁邊伸過來,哆嗦著,急切地探索著,她感到他的手是冰涼的,自己的身體也是,那罪惡的手在屁股蛋上逡巡,用力地揉捏,然後…… 大馬不再出聲,他安靜地躺在那裡,睜大眼睛,籍著月色,他貪婪地看著跪在自己身旁、一絲不掛的周舟。她很聽話,也很賣力,她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專心緻志的神情。這神情就像一劑良藥,迅速地撫平著他剛才那種焦躁的心情,她領會動作要領很快,不一會兒,就把他侍侯得很舒服。 算起來,近在咫尺的周舟是他帶上炕頭的第十一個女人,他勾引女人,也享樂於受女人勾引,他覺得,正是靠著這些,才有滋有味地活到了今天。看見個有些姿色的女人,他就按捺不住,千方百計地也要將她弄上炕頭不可。 多少年來,在這上面他得過手,也栽過跟頭,但卻從沒像今天這樣慌亂過。從上午,周舟這條鮮美的大魚終於咬鉤開始,他心裡就止不住的鬧騰,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他反覆算計著該怎樣才能好好地享受這頓美餐,他擔心會出現什麼變故。 大世面他見過,城裡的妞兒也嘗過,他分得清醜俊好歹,掂得準誰輕誰重,他知道周舟這條大魚的份量,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像周舟這樣的姑娘在城裡也是萬裡挑一的。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他打心眼裡感謝文化大革命,能在他正值如虎年齡的時候,往他所在的窮鄉僻壤送上這麼一塊嬌艷欲滴的鮮肉。他明白,今天晚上這事兒是過了這村就沒這店的景色,抓不住就算溜了,沒地方找後帳去。非他媽的干她三次不行!他這樣打算著,相信自己的能力,充分地相信,他有這方面的佳績。 然而,他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臨到此時他會陽痿得這麼厲害。 剛開始,似乎還有點意思,但接下來就不行了,尤其是當她在他的劇烈揉搓下不停地扭動著她的軀體,呻吟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感到明顯地力不從心了,最後,當周舟叉開她那渾圓的玉腿,高高地抬起那誘人的屁股,完完全全地將她的隱秘暴露在他面前,只等著他插入的時候,他徹底垮下來了。 他從沒見過如此美艷的肉體,做夢也沒見過。周舟那奪人魂魄,令人震撼,美輪美奐的肉體,使大馬有生以來頭一次在女人面前感到自慚形穢。他氣憤,他怨惱,他起急,他發狠,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溫香在握,軟玉滿懷,讓他慾火中燒,卻又無可奈何,他沒有了著數,他服了,他頭一次領教了由女人的肉體引發出來的恐懼。他絕望地照準她豐滿圓潤的屁股,狠狠地咬了一口…… 月色下,周舟那白嫩的肌膚發出脂玉般的光澤,他想看清她的臉,伸出手,撩開她披散下的一抹黑髮,但一鬆手,那頭濃密的黑髮,又傾瀉下來,他托正她胸前晃蕩不停的那對碩大的乳房,揉捏著上面彈性十足的乳頭。她又一次呻吟起來了,手上的動作更快了…… 「別弄了,」他拿開她的手,坐起來,「看樣子是不行了。」 他心裡明白,他的雞巴比他誠實,面對她的肉體,甭提勃起奮進,勇於侵佔,它嚇得自始至終都不敢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你把那瓶白酒給我。還有花生米,就在外屋的鍋台上。」 周舟還是愣了一下,滑下炕,白酒是不是他最後的春藥?她端著那盤花生米回到屋裡時,大馬正在穿衣服。「你也穿上吧。」 她把衣服穿好,坐在他的對面,忐忑不安地等待著,沒有料到的場面,似乎有理由說了不算。 「你還喝麼?」他把酒杯向她一推。 「我,不喝。」她將酒杯推回去,不安地望著他。 「你喝吧。」大馬端起酒,喝了一口。「你是不是在心裡罵我呢?罵我是個畜生!」他突然問。 「沒……沒有。」 她驚訝地瞪大眼睛,否認著,要壞事! 「沒啥,罵就罵了,罵了也該著。」他又喝了一口,「本來這事兒就是畜生辦的事兒,比畜生還不如!」停了一下,他又說了,「今天咱們這事兒就算完了,我弄不了你,你太俊了,俊的嚇人……說實在的,我以前沒有這樣過。」 她木然地點頭,她相信他的話是真的,心裡稍微塌實了一些,她期待著他看著好,盼他能快點把話題轉入正題。 大馬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苦笑了一下,「招生表帶著吶嗎?」 「帶著呢。」周舟趕緊掏出那張疊得整整齊齊的招生表,遞過去。 他拉亮電燈,接過招生表看了一眼,平整地鋪在炕沿上,然後轉身,從炕頭的一個布包裡掏出兩枚直徑象乒乓球大小的公章,又從窗台上取過印泥盒,把公章放在裡面蘸了一下。 周舟看著這一切,心裡緊張地怦怦直跳,眼看到手的勝利,她渾身上下戰慄著。她抑製著自己恨不得立即飛出這間屋子的衝動,靜靜地佇立在那裡,勝利在握,她想善始善終。 「你走吧。」大馬低著頭,歎息,「明天起,你就別出工了。」 她感到一陣釋然,渾身輕鬆,「我走啦。」 他脖一仰,喝下去一杯酒,微微點了一下頭。 屋外,月白風清,是個想什麼就能得到什麼的夜晚!周舟漫步在村邊的田野上,伸展雙臂,盡情地呼吸著這鄉村之夜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氣,週身的熱血在沸騰,她感到特別興奮。她想,這是她生平第一次自己設計,自己實施,並且獲得成功的勝利,一切都明碼標價,雙方都付出又都獲取,公平交易,值!是大馬教會她,該怎樣利用本能去得到,他沒有理論,沒有循循善誘的說教,而是以身作則地邀請她,共同參加了一堂生動的、難忘的實踐課,這一課程的內容改變了她的命運。這次送貨上門的收穫真不少。 回到宿捨,她打來一大桶水,脫下衣服,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起來,臀部生疼,她扭頭一看,一圈紫青的牙印在雪白的皮膚上,刺眼又醒目,恥辱的印記,直徑和那兩枚公章差不多。肯定會褪下去的,她一面往那地方塗抹著香皂,一面安慰自己,她擔心的是,那同樣印在心裡的恥辱印記何時才可以消退……生活還要繼續,更好地生活下去! [全文完] |

- 【全集】舞會之後(全)
- [經驗故事]健身房豔遇
- [人妻熟女]幫妳老公滿足妳
- [群體換伴]快樂病棟
- [不倫戀情]幹了兒子的女友
- [經驗故事]西藥房的愛與呻吟
- [經驗故事]咪咪系列∼月圓之夜的放縱
- [不倫戀情]乾媽也要人搞
- [不倫戀情]我和四哥的性愛往事
- [人妻熟女]淫蕩少婦
- [學生校園]形體課的教師
- [動漫修改]美少女戰士外傳9
- [玄幻仙俠]屍通
- [不倫戀情]誘人的繼母媽媽
- [科學幻想]聖女修道院14(2)
- [人妻熟女]人妻、情事的報酬
- [職場激情]鄉村的家庭生活
- [不倫戀情]玩電腦中的媽媽
- [不倫戀情]誘姦-父女情懷
- [暴力虐待]少婦銷魂夜
- [學生校園]校園大件事之裸人質
- [職場激情]女友的出軌1~2
- [職場激情]高職家庭快樂多(1-8)
- [人妻熟女]十個女人十個騷
- [人妻熟女]我把乾娘家母女三人一鍋端了
- [職場激情]銀行的騷女雅琪
- [暴力虐待]淫艷屍姬
- [其他故事]春節走親戚成就了我的亂倫
- [人妻熟女]農村校園裡
- [人妻熟女]市場風雲驚豔 9-12
- [人妻熟女]極品美女一起幹
- [職場激情]豐滿的精神病女患者和打掃衛生大姐
- [人妻熟女]我和媽媽的親密經曆
- [人妻熟女]夫妻交換樂趣
- [職場激情]醫生玩弄女病人
- [暴力虐待]《惡》(全)
- [經驗故事]好室友(全)
- [人妻熟女]退休的王阿姨
- [暴力虐待]輪暴 降魔天師 - 馬小玲
- [不倫戀情]浪漫的換妻遊戲 1 (2/2)
- 本錢本色21-30 (2/2)
- [職場激情]姐夫的榮耀 (第一部 1—18集完) 作者:小手 (10/33)
- [人妻熟女]從精神出軌,到肉體淪陷,嬌妻陷入換妻泥潭的心路歷程 (2/2)
- [玄幻仙俠]神鵰俠侶•逍遙篇(九)
- [暴力虐待]筱雯野外被姦
- [不倫戀情]老公的總經理
- [職場激情]性開放D市界 (01~20) (1/5)
- [不倫戀情]媽媽的探親假D
- [人妻熟女]熟女櫻的告白∼老公設計我喝醉讓人玩
- [不倫戀情]與表弟的偷情
- [不倫戀情]我和我同學母親的故事
- [職場激情]第一次
- [職場激情]女兒的女朋友
- [職場激情]嬌妻的貴婦同學
- [其他故事]雅雅的預備生訓練日記 (三) 破處內射成女人
- [職場激情]床上運動
- [不倫戀情]絲襪美母之醫院風雲
- [人妻熟女]你消失的第10天
- [學生校園]淫蕩的學妹
- [不倫戀情]目擊媽媽在公車被群姦
小說區 隨機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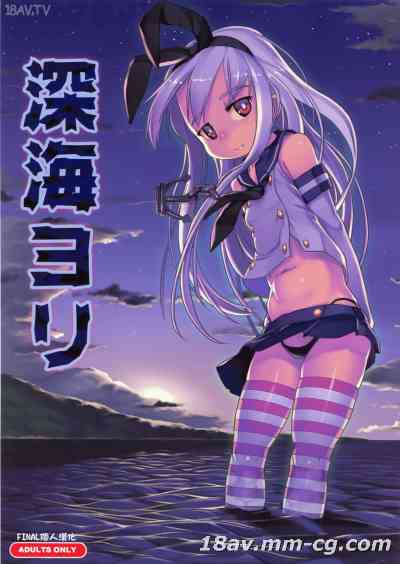


















![Bejean On Line 2010-04 [Hassya]- Momoka Kano](https://fchost1.imgstream2.com/s/wp/wp1446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