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友站 番號最齊 新作上架最快!(每天更新百部AV)
請使用轉址到網站新介面模板瀏覽, 10 秒后,
会转跳到 ==> https://18av.mm-cg.com
小說名稱:[人妻熟女]別人的床上操著別人的妻子
文字放大: 自訂文字大小: 行距:|
這段故事是我的真實經歷,現在把它寫下來,不知是為了追悔,還是為了擺 脫這愛與痛的回憶……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這個普通的南方城市的一家工廠。工廠幾乎在城區 與郊區之間,交通也非常的不便,報到的第一天,坐著滿是污泥的公共汽車,搖 搖晃晃,忍受著售票員與乘客吵架的怒吼聲,望著窗外的路邊雜草,情緒真的低 落到了極點。 按照慣例,剛剛分配的學生都要到車間裡實習一年。我被分配到一個裝配車 間,任務就是打雜,幫助班組裡的工人配件,清洗成品。每天上班,三點一線: 宿捨、食堂和車間。 車間裡的氣氛是典型的國營單位,效率低下,人浮於事。一天中我有一半的 時間是躲在什麼地方睡覺或看報紙,要不然就是聊天打屁。但是和車間裡的工人 們卻又沒有很多的共同語言,不外乎東家長西家短的爛事,實在是厭倦。 不過班組長老張還不錯,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中年人,對我也比較照顧。正所 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車間的人平均收入都低得可憐。比如老張,在這廠裡已 經工作了十幾年,基本工資居然只有一百多塊,獎金每個季度發一次也不過幾十 塊錢。我就更不用說了,工資只夠吃飯的錢,連花生加一瓶啤酒也是好大的享受 了。 無聊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已經上班一個多月了。一天上午,我正在看報紙 的時候,忽然班組裡的幾個女工人簇擁著一個少婦走了進來。 大家七嘴八舌地問著她,聽了一會兒我才明白,原來她是質檢科的,負責我 們班組的產品,前些天她休產假,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我遠遠的看著她,上身是 紅色的風衣,下身是一條黑色的緊身牛仔褲。黑色的高跟鞋顯得她個子很高,妝 化得比較濃卻很得體。因為剛剛生過孩子的關係,身材很豐滿,尤其是乳房高高 的隆起。 她忽然向我這邊看了一眼,漆黑明亮的眼睛透著高雅和恬淡,我趕緊低下了 頭。伴隨的高跟鞋的清脆聲音,她走到了我的身邊:「你是剛來的吧?」 「是,實習的。」 「喲,那你是大學生嘍。跟哪個師傅呢?」 「錢師傅。」 「那我可還是你的師姐呢!」 她走後,淡淡的香水香味還繚繞了許久。從大家的談話中我知道她叫薛莉, 也是大學畢業,已經在這裡工作了三年了,是廠裡出名的美女,衣著打扮也總是 很新潮。不過我覺得更吸引人的還是她脫俗的氣質,令人奇怪的是不知為什麼她 的丈夫卻是一個名聲不是很好的普通大集體工人。也許是各有所愛吧,班組裡的 趙姐說。 就這樣,薛莉重新走進了我們班組,給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抹亮色。 時間慢慢的渡過,我和她也慢慢的熟悉起來。我們總是有很多相同的話題, 更巧的是我們的生日居然是同一天,差別是她比我大了三歲。她知道我是住單身 宿捨,沒有什麼好吃的,便經常做些好吃的東西,用一個精緻的小飯盒帶給我, 粗心的我經常忘了還給她,所以在我的宿捨裡經常堆了好幾個飯盒。當我謝謝她 時,她總是說:「客氣什麼,我不是你的師姐嗎!」 她女兒出世一百天的聚會時,我們班組的每個人湊了二十塊錢的紅包給她, 她卻執意私下裡要還給我,我不收,她又隨後買了一個漂亮的小打火機送給我, 原因是她認為我一個人在外面不容易。她還經常說,有機會時給我介紹一個女朋 友,省得我總是麻煩她。 我們幾乎無所不談,但是每次談及她的丈夫和家庭時,她卻總是迴避開這個 話題,眉宇中隱隱閃過一絲憂傷的影子,使我覺得在她平靜高雅的表面下,一定 有什麼事情她不願講出來。 初夏的一天,她沒有上班,託人來說病了。雖說只有一天沒有見到她,我卻 覺得好像空蕩蕩的。第二天,我再見到她時,吃了一驚,雖然她還是化了淡妝, 但卻掩不住憔悴的臉色和略顯紅腫的眼睛。大家問她,她只說感冒了,但我知道 絕不是這樣。 我悄悄的問她:「師姐,我知道你沒有感冒,能跟我說說是怎麼回事嗎?」 她慌亂地躲開我的眼睛,低下了頭,用手指戳著桌面,沒有講話。一天就這樣過 去了,她都好像有意無意的躲著我。 因為有一批訂單沒有完工,晚上要加班。在餐廳打飯的時候,她看旁邊沒有 人,忽然對我說:「小于,晚上9點在車間後面等我好嗎?」我點了點頭,她便 低頭離開了。 後面的幾個小時,我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我隱約知道她將會跟我說一些什 麼,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態度去聽,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9點,我如約來到廠房後面的草地。銀色的月光透過樹葉直瀉下來,斑斑的 落在地上,週圍很靜,只聽到蟋蟀的鳴聲。她已經站在那裡等我,一身淡黃的套 裙,肉色的絲襪和白色的高跟鞋,襯托著她豐滿俏麗的身影。鬆鬆挽起的髮髻, 還帶著香波的氣息--看來她剛剛在廠裡洗過淋浴。我的心忽然狂跳起來,預感 到今天晚上會有什麼事發生。 「給我一支煙好嗎?」這是她的第一句話。正如我所猜想的,她開始跟我說 起了她的故事,而且正是以前她所從不願提起的話題。平靜的語氣,好像是在講 述一個與她自己無關的事。 三年前,她畢業來到這裡,是公認的廠花,追求者多得一大串,可是卻有一 個黑影盯上了她。這個人就是她現在的丈夫,他是一個有名的惡霸式的人物,同 事和領導都被他打過,三天兩頭就要進公安局;好好的正式工作也丟了,進了大 集體工廠。 薛莉又怎麼會看上這種人,堅決拒絕了他。可是沒有想到惡夢就此開始了, 從跟蹤、恐嚇,到去薛莉的父母家裡胡鬧,毆打任何與薛莉有聯繫的男人。在這 種淫威之下差不多一年,薛莉流淚看著自己日漸衰老憔悴的父母,不得不決定屈 服--和他結婚。 新婚的時候,他還裝得像個人,可是沒過多久便又恢復了原樣。好吃懶做、 喝酒賭博,薛莉稍有不滿,便惡語相向,甚至是動粗。薛莉是個要強的女人,在 別人面前不願說起這些,因為她不想再讓父母傷心,每次都說他對自己很好,傷 心的淚只能一個人偷偷的流。 有了孩子之後,薛莉以為他可能收斂一些,卻沒有想到,一天上午她回家取 東西時,竟然發現他與另一個妖艷的女人正在床上鬼混。 被發現以後,他更加肆無忌憚,公開地把不同的女人帶回家,而且竟然逼迫 薛莉與他的狐朋狗友上床,還美其名曰互不吃虧。薛莉寧死不從,結果就是經常 的惡罵和毒打…… 月光照在她恬靜的臉上,發出淡雅的光輝,除了她微微抖動的睫毛,誰也看 不出她剛剛講述了那樣的一段經歷。我的心痛的快要碎了,我怎麼樣也想不到在 她高雅寧靜的外表下面,竟然是忍受著這樣的不幸與痛苦。我不知道應該說些甚 末,只能默默的站在她背後。 這樣過了許久,她輕輕的轉過身來,問我:「小于,你喜歡我嗎?」我的頭 一陣暈眩,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雙手卻下意識地攬住了她的雙肩,她順勢滑入了 我的懷中。 我的呼吸幾乎不能繼續,我們的嘴唇終於吻在了一起,她的唇豐滿而柔軟, 但卻是冰涼的。我撫摸著她的背,她顫抖著,我終於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說: 「我的師姐,我喜歡你,真的,從一見到你的第一次起就不能控製我自己去喜歡 你。」 她不說話,用小狗一樣涼涼的鼻子尖蹭著我的臉,繼續用唇堵住我的嘴…… 我們這樣相擁著站了好久,終於她對我說應該回去了。看著她騎住自行車遠去的 身影,我只有心痛,因為我不知道她回去後又會面對那個惡棍怎樣的摺磨。 第二天,我們在班組裡再見面的時候,盡管彼此都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 是我能感覺到她明顯的變化。俏麗的臉上光彩照人,偶爾眼角會飄過一縷初戀的 少女才會有的羞澀與不安。 就這樣過了幾天。這天是五一節,廠休日。同屋的小劉去另外的一個小城看 女朋友去了,我正在宿捨裡面看書,忽然樓下的收發室叫我的電話,是薛莉打來 的。她說:「我去看看你行嗎?我又做了一點好吃的給你。」我說:「當然可以 了。」於是我們約好晚上7點鐘在宿捨樓下見。 剛下過雨的傍晚,空氣清爽得很,心情也似乎從悶熱的牢籠中掙脫了出來。 當我見到她時,不禁驚訝於她的美麗,一身銀灰色的套裙顯得風姿綽約,黑 色的絲襪和高跟鞋又是那樣的性感撩人。她見到我出來,悄悄地笑了。我帶著她 走進樓裡,路過收發室的時候,那個守寡的小女人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看著我們。 管她呢! 一進我的房間,我立刻便反鎖上門,兩個人緊緊地擁在了一起,狂熱親吻著 對方。薛莉的臉頰潮紅,星目迷矇,我摟著她火熱的身體,不能自持。 我們跌坐到我的床上,她呼著芬芳的氣息,輕輕地問我:「弟弟,你想要我 嗎?」我喃喃地回答:「想啊,姐姐。你知道嗎,這是我的第一次。」事實的確 是這樣,在大學裡我也吻過別的女孩子,但是真正的肉體接觸卻從未有過。 薛莉似乎有一點驚訝,隨即嬌笑了,說:「那麼我來要你好嗎?」我隨她的 手臂躺在床上,她伸手熄了燈,但是因為時間還早,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清一 切。 蚊帳也放了下來,薛莉輕輕的伏在我身上,雙腳蹬脫了鞋,我央求說:「姐 姐,不要脫鞋好嗎?我喜歡你穿高跟鞋的樣子。」她羞澀地點了點我的鼻子說: 「你這個小色棍。」但是卻又把鞋重新穿上了。 輕輕地,我的褲帶被解開,陰莖一下子跳了出來,龜頭紅腫的樣子把我也嚇 了一跳。薛莉說:「原來你的寶貝這麼大呢!」我只好說:「因為我愛你呀!」 她撩起了裙子,露出黑色的內褲,我便幫助她把它脫了下來,薛莉隨手便把 它套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我的手撫摸著她的屁股,豐滿圓潤的感覺,她的腹部依 然還是很緊湊,不像是個少婦的樣子。 薛莉堅持不讓我看她隱秘的地方,我也只好作罷。我的手又再停在她的乳房 上,因為她還在給孩子哺乳的關係吧,令人難以相信的豐滿。 薛莉低聲地呻吟著,分開兩腿,用手扶著我的陰莖,輕輕地坐了下去。我看 著自己粗大的陰莖慢慢地消失在她的陰毛下面,隨即感到天旋地轉,好像進入了 另一個世界,那樣的溫暖,那樣的濕潤,好像有難言的一股電流流遍了全身。 薛莉趴在我的身上,開始輕輕的蠕動著她滾燙的胴體,溫熱的呼吸吹在我的 頸間,癢癢的但是好舒服啊!我的手摸著我們身體的結合部位,清楚地感受到我 的陰莖正在她陰道裡進出,伴隨著濕濕的體液,我的身體似乎飄了起來,意識也 似乎有些不清楚了。 伴隨著薛莉越來越高的呻吟聲,我們接合的速度也越來越快……終於,一陣 麻麻的快感從腰際和雙腿直擊腦後,我的陰莖在薛莉的體內劇烈地跳動起來。薛 莉嬌哼了一聲,伏在我的身上好久好久。 當我們想起應該起來的時候,夜色已經偷偷地降臨了。我打開燈,看著我親 愛的姐姐,薛莉一臉的嬌羞,埋怨我說:「你看你,流了這麼多,我的裙子都印 上了!」 我看了一下,的確,她的裙子後面也打濕了一大片。我一把攬過她的腰肢, 說:「就算我給你留的記號吧!」 她笑道:「你都壞死了,誰稀罕你的髒東西。」 我癢著她的肋間,說:「真的髒嗎?」她掙脫著,但是沒有成功,終於她伏 在我的懷中,閉著眼睛小聲說:「不髒,我喜歡……」 從這一天起,我們開始體驗著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生命也似乎變得豐富起 來。但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也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做愛, 她的家裡不可能,我的宿捨因為是合住,也是不行的。 就這樣幾天後,薛莉忽然偷偷的跟我說:「今天晚上我們在工廠的操場那裡 見。」 操場是在廠區的邊上,每年除了開運動會以外,平時根本沒有人去,四週都 是密密的樹林,很寂靜。我提前很久到了那裡,只有晚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 薛莉終於翩翩而來,我摟住她說:「姐姐,我想死你了。」 我們親昵了一會兒,我的陰莖漲了起來,頂著她的腹部。薛莉笑了,用手指 輕輕地滑過那裡,說:「又不老實了。」 我聞著從她頸項中傳出的暖暖的肉香,回答說:「怎麼能老實呢?除非是太 監。」薛莉說:「想要我嗎?」我說:「當然想了,可是沒有辦法啊!」她說: 「這樣也可以呀!」 我很好奇怎麼可以,薛莉彎腰脫下了連褲絲襪右腿邊和白色的內褲,然後解 鬆了我的褲帶,用她柔軟的手拉出了我的早已粗大的陰莖,微微地喘息說:「來 吧,寶貝。」 她靠在樹上,向旁邊抬高右腿,我身子向後少傾,原來真的很容易就插入了 她的陰道裡面。我左手抬著她的右腿,右手攬著她的屁股,她雙手緊緊地摟著我 的背。 我開始抽動陰莖,薛莉開始呻吟,喃喃地說:「弟弟,你操我吧,狠狠地操 我……」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從我平時那樣端莊高雅的姐姐口裡說出來的,興奮 到覺得太陽穴都在發脹。 我們都可以聽到我們的肉體相交時發出的那種濕潤的淫糜的聲音,兩個人的 舌頭攪在一起,吸吮著相互的渴望和瘋狂。 過了一會,忽然有雨點飄了下來,薛莉從皮包裡拿出摺疊傘,撐了起來,罩 在我們的頭上。聽著雨滴打在傘上清脆的聲音,我們更加投入,因為不需要在乎 會被別人看到。 愛撫著、抽動著,姐姐也慢慢地蠕動著身體來配合我的動作。終於我達到了 頂峰,一股熱流射向了她的深處。忽然姐姐輕輕地抽泣了起來,我很害怕,以為 有什麼不對。 過了一會,她不好意思地說:「我有了高潮了,真的,這還是我結婚後的第 一次有呢!好舒服。」 我問:「那怎麼會哭呢?」 她說:「不知道,只是忍不住要哭。」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廠區外面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們愛的蹤跡。有一天晚 上,我們照例在一塊草地上幽會,我坐在地上,伸平雙腿,薛莉面對著我,將短 裙提到腰部,跨坐在我的身上,我們又緊緊地交合在一起。 我撫摸著她完全露在外面的雪白屁股,忽然我發現對面有一個幹部模樣的中 年人在遠遠地窺視著我們,我很緊張,偷偷地將一塊石頭摸到身邊,對薛莉說: 「有人在看我們。」她回頭看了一眼,說:「不管他,讓他看去,過過眼癮。」 說完,便加大了身體起落的幅度。 那個人沒有什麼舉動,只是手伸入了褲子裡在上下的動。被人看著做愛,居 然是這樣的刺激,很快我們就都達到了高峰…… 正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盡管我們都很注意平時在單位裡面盡量作 出一切如常的樣子,但是感情這東西是沒有辦法掩飾的。尤其是薛莉,經常情不 自禁地流露出親昵的表情和動作,有時趁著沒人的時候她會來吻我。漸漸地,有 一些風言風語便流了出來,但是她卻並不是十分的在意。 我經常很痛苦,我愛她,愛她的人,也愛她性感無邊的肉體,但是我又不知 道我們究竟會走到哪裡。我也不知道我能否拋開家庭與社會的壓力,以一個第三 者的身份與一個比我大三歲並有了孩子的她結合。而且,她丈夫的陰影總是擺在 我們之間。 我們曖昧關係的公開程度,終於在一次達到了頂點,經過是這樣的: 班組裡的小曲結婚了,我們大家都去參加婚禮。喝過喜酒之後,跑到洞房去 鬧,由於人很多,房間又很小,大家很擠,我和薛莉便靠著牆、坐在床上和大家 聊天。因為喝了酒,很興奮,她偷偷地從身後把我的右手拉進了她的後腰的裙子 裡,因為這條裙子是鬆緊帶的長裙,很方便就伸了進去。 我不由自主地盡量向下面摸去,姐姐她輕輕地靠著我,欠著一點身子。我的 食指摸著她的肛門,很緊湊的花皺在我的手指下輕輕地收縮著,眾目睽睽之下作 著這樣的事,我的心狂跳著。 忽然姐姐竟忍不住呻吟了出來,有的人似乎聽到了這性感的聲音,很奇怪地 看著她,但是又明顯意識到了什麼,趕緊把目光移開。 從小曲的家離開之後,我問她:「怎麼出那麼大的聲兒呢?」她說:「人家 忍不住嘛!幹嗎摸那裡,感覺好淫蕩,我都濕透了。」 我們兩人在附近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馬上迫不及待地性交起來。從此,我 們的事幾乎到了半公開的狀態。 轉眼到了秋天,姐姐的女兒已一週歲了,我買了一些禮物,去姐姐的家裡參 加慶生會,家裡早到了七、八個人,都是她和她丈夫的朋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她丈夫,外表卻是很普通的一個人,頭髮和鬍碴比較重而已。自始至終,他都用 一種特殊的眼光看著我,我只好硬著頭皮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 終於聚會結束了,其他的人紛紛告辭。大家走光了以後,他說要去打麻將, 對我說:「老弟,你再多坐一會兒吧。」便穿衣走了。 我總是有一種不好的感覺,也想離開,但是姐姐卻擋在門口不讓,說:「再 陪陪我,好嗎?」我只好留下。 姐姐拉著我坐在床上,我們自然而然地擁抱在一起,我把她的褲子褪到了膝 蓋,然後跪在床上,抬高她的雙腿放在我的肩上,快速地插入了她早已濕潤的陰 道。在別人的床上操著別人的妻子,感覺竟是這樣的奇妙難言。 不知道什麼時候,躺在床邊的她的女兒醒了,瞪著油黑的眼睛看著我們,姐 姐一邊呻吟著,一邊撫摸著女兒說:「小……寶貝,叔叔在……操媽媽,你不高 興了,是嗎……」 在她女兒的眼前,我們匆匆地結束了親熱,我便離開了。 第二天,姐姐沒有來上班,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很是擔心,有一種不好的 預感。吃晚飯的時候,我剛剛走到食堂門口,被人一下子架到了一邊,是她的丈 夫和另外兩個凶神惡煞般的人物。我的心一沉,知道一定要不好了。 他拿了一把刀,頂著我的脖子說:「老弟,昨天我讓你陪陪我老婆,你幹了 什麼?」我說沒有什麼。他掏出了一盤錄音帶,狠狠地說:「操,你們他媽的也 太投入了吧,我的錄音機就在床下你們都聽不到。你們的那點爛事,我早就知道 了,就是要點證據。」我沒有辦法再說別的了。 他說:「晚上8點,到我家,我再收拾你們。如果你敢不去,我就閹了你, 再把你們搞得臭遍全廠。」 懦弱的我不敢不去。當我走進她的家時,我看到她丈夫和那兩個大漢坐在桌 邊,而我的姐姐竟然全身赤裸地蜷縮在床上,身上青腫了幾處。 她丈夫拿出了刀,對她說:「如果你不想我當著你的面把他的雞巴割下來, 就老老實實地按照我說的做!」 姐姐流著淚,沒有動。另外兩個男人居然脫光了自己的下身,一個撲到薛莉 的身上,兩手使勁握著她的乳房,開始像餓狗一樣輪流吸吮著她兩粒乳頭,她緊 閉雙眼,屈辱的淚水唰唰地流著;另一個拉開薛莉的雙腿,把手伸到她陰部上褻 弄著,一會捏捏陰唇,一會擦擦陰蒂,一會摳摳陰道,姐姐渾身顫抖,默默承受 著兩個色狼的污辱。我被迫看著這一切,但我不敢反抗,因為這些人什麼都做得 出來。 那個人在陰戶上玩弄了不一會,就一手撐開姐姐的陰唇,一手握著粗黑的陰 莖深深地刺入了姐姐的柔弱的軀體,她悶哼了一聲,無奈地搖動著頭。我看著那 根陰莖在我心愛的人的陰部抽插著,清晰地傳來肉體碰撞的「啪啪」聲,她的陰 唇被帶動著裡外翻動,似乎想推出又想吸入那根陰莖。 她丈夫在旁邊淫邪地看著,說:「騷屄,讓你跟我哥們幹,你還她媽的裝處 女。你們不是相愛嗎?就讓你的情人看看你怎樣被人操,比婊子還不如!」 那個男人狠狠地操了一陣子,便把一大泡精液射進薛莉的小穴裡,剛把陰莖 拔出來,另一個男人又接著插入她的陰道。姐姐的臉色開始泛紅,呼吸也急促起 來,肉體的快感是無法控製的,她死死地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出聲。 看著自己心愛的姐姐被別的男人壓在身下,陰道裡吞吐著一根昂首怒目的粗 壯雞巴,在快速而強勁的抽插下不由自主地慢慢滲出淫水,而我竟然感到陰莖開 始膨脹。我拼命地壓製著,但還是沒有用,天哪,我這是怎麼了! 惡夢不知道持續了多久,終於一切都結束了…… 幾天後,她離開了這個城市,只聽說去深圳了。而我也無法再面對週圍的人 們,通過考研又回到了學校。 幾年已經過去,而這段回憶卻仍難以忘卻。那份愛,那份痛,我將永遠無法 擺脫。 |



- [群體換伴]淫亂的徐娘
- [經驗故事]淫蕩的平安夜
- [經驗故事]我和一個女孩的絲襪故事
- [不倫戀情]表叔嫖妓
- [經驗故事]與護士妹的真實相遇
- [學生校園]大學生買小褲褲的面交經驗
- [經驗故事]有些事要偷偷的幹才爽
- [經驗故事]吃飽的陽具
- [群體換伴]猛上女友的朋友
- [經驗故事]公車上的MM
- [經驗故事]長途臥鋪車
- [群體換伴]三姐妹同侍一夫
- [科學幻想]人魔之間
- [經驗故事]荒野艷譚
- [職場激情]漂亮老婆白白被送貨員幹了一下午
- [玄幻仙俠]仙俠魔蹤第一集
- [人妻熟女]在公車上幹人妻(公車上幫我射精的中年美婦)
- [經驗故事]王子和三個小女孩
- [學生校園]淫蕩高中妹5-7
- [學生校園]大學美女打工 2
- [經驗故事]試探“後院”
- [人妻熟女]鄰居的美老婆(陳太太的肉體)
- [職場激情]一個女作家的經歷
- [不倫戀情]姐姐讓我知道什麼是“屄”
- [長篇連載]聰明玲莉13上+下
- [人妻熟女]準備好紙巾凝聽的故事《妻子就這樣失身了》
- [職場激情]三天假期(轉貼)
- [人妻熟女]色情作家乖乖女
- [職場激情]姐姐與他同學
- [學生校園]大學裡糜爛的日子
- [暴力虐待]護士妻子被強姦(轉載)
- [不倫戀情]浪媽色姐
- [暴力虐待]我的 SM 經歷
- [不倫戀情]一時雲起之岳母1-9
- [不倫戀情]舅媽的性愛課程
- [不倫戀情]媽,我要射了
- [附圖小說]淫亂的宿舍(超犯罪催眠術)
- [職場激情]女警的調教(全)
- [職場激情]禪杖下的嬌娃
- [人妻熟女]小夫妻的淫蕩事之「淫亂樂翻天」1-10
- [不倫戀情]我家的女人 1-5
- [其他故事]夢之廊
- [暴力虐待]煉獄天使 1-23集 (完) 作者:半只青蛙&知樂 (28/34)
- [玄幻仙俠]公主復國記 (9/13)
- [人妻熟女]老婆疑似出軌的經驗(1一24)(全文完) (1/3)
- [動漫修改]【阿拉克尼】異化 (6/9)
- [暴力虐待]電車肛辱
- [職場激情]壹次約炮經歷
- [人妻熟女]我與對門的少婦
- [經驗故事]交換母親【完】
- [不倫戀情]怨母與淫亂子
- [職場激情]理想的調教
- [人妻熟女]女生菲菲1-11 (1/4)
- [人妻熟女]與少婦同事的兩次性愛經歷
- [職場激情]迷惑的處女
- [學生校園]淫慾女室友
- [人妻熟女]我上的美少婦極淫
- [科學幻想]我下載到了女友的A片
- [不倫戀情]內射表嫂
- [人妻熟女]入贅女婿的秘密
小說區 隨機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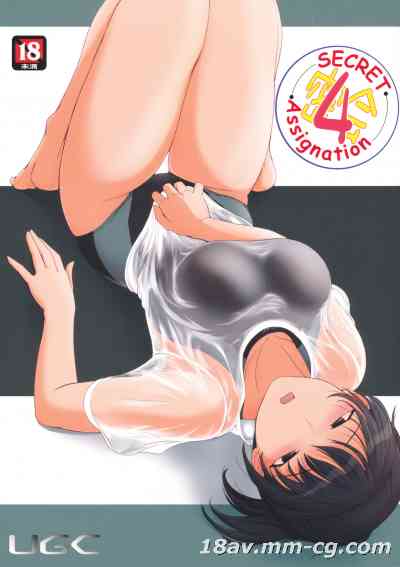


















![Bejean On Line 2008-12 [Cover]- Akiyama](https://fbhost1.imgstream2.com/s/wp/wp1427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