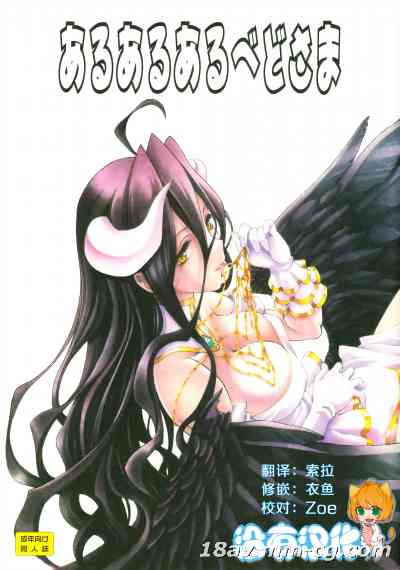【廣告】友站 番號最齊 新作上架最快!(每天更新百部AV)
請使用轉址到網站新介面模板瀏覽, 10 秒后,
会转跳到 ==> https://18av.mm-cg.com
小說名稱:[人妻熟女]我和嬸母
文字放大: 自訂文字大小: 行距:|
上世紀70年代末,農村開始聯產承包。我家是非農業戶,沒有土地。高考後的焦慮幾乎讓我精神崩潰。一天正在村頭徘徊,嬸母荷鋤而來,心疼的撫摸著我的臉說:「瘦多了。」於是我和嬸母一起去了她承包的地。一天下來居然感到精神很充實,於是我就每天隨她去勞動。 嬸母是個俊俏的農婦,勤勞、善良,她有個引人注目的豐腴圓潤的大屁股。 鄉下人都認為,屁股大的女人生男孩兒,而嬸母偏偏連續生了3個女兒。叔是個木匠,沒讀過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卻在他腦子雷根深蒂固。他整天東奔西走打工掙錢,積攢些家業,唯一不順心的是嬸母沒給他養個兒子。按說,生男生女是兩個人的事,可叔不管那些,每當喝點酒就發洩對嬸母的不滿,說:「活著沒意思,這麼多家業連個繼承的也沒有。」嬸母只能逆來順受。 嬸母那年38歲,我19歲。她不怎麼避諱我,在田間方便開始還走遠幾步,後來只是轉過身去。嬸母雪白圓潤的大屁股讓我亢奮。終於有一天中午在倉房嬸母哈腰舀米的時候我從後面抱住了她。 嬸母很平靜,撅著屁股任我摸弄。後來她轉過身正面對著我,臉上有點紅暈。 當我將手摸在她陰部的時候她便解開了褲腰帶。在嬸母的幫助下我的陰莖插入她的生殖器�。我是初次,只感到嬸母的B很潤滑,很綿軟,好像�面都是水兒。 和嬸母搞「破鞋」這是天大的不齒之事,事畢我開始惶惶然。可嬸一直安慰我。惶恐歸惶恐,可誘惑總禁不住。那幾天和嬸母每天都要有一次甚至幾次,田間、地頭兒,倉房、炕上。嬸母從不拒絕,有求必應。一天在嬸母的炕上,我正趴在嬸母身上肆虐,聽見大門響。我從玻璃�看見叔回來了,立即嚇得面如土色。 嬸母欠起赤裸的上身看見是叔,邊重新躺下邊說:「別怕,沒事!」接著喊到:「別進來,小X在這呢。」一向苛刻暴虐的叔遲疑一下,在院子�走了幾圈,放下工具背起筐,關上大門出去了。 我如遇大赦,拔出陰莖顧不上等嬸母給我擦拭便惶惶然穿褲子。嬸母笑著拽住我說:「沒事,玩完再走。」事畢嬸母對我說:「咱們的事他早就知道,他就是想要個兒子。叔頑固的認為:野種都是小子而且聰明。他唯一不放心的是我的種算不算野種。 嬸母是個很稱職的女人,我離開家上學的時候她的肚子已經有些鼓了。第二年嬸母果然生了個白胖的兒子。我對是不是我的種一直懷疑,因為在我和嬸母性交的同時,叔也報復性的和嬸母性交。只是嬸母說:「他的很小,也沒多少水兒。」 嬸母生了兒子,似乎對我更好了,可叔則不冷不熱。以前每當我來的時候她都藉故躲出去,現在,每當放假去他家,他大多流露的是反感,更不用說躲出去了。 有了這事是很難忘卻的,何況嬸母對我好。 終於有一天叔外出了,嬸母把我找到她家,在性交的時候嬸母對我說:「以後咱們得加小心,再不能讓你叔碰上了。以前他想要兒子,巴不得你一天操我八遍。現在有兒子了,他就不讓了。他還說兒子是她的種,和你沒關係。」誰的種我並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嬸母的態度:「你是什麼意思?願意讓我幹嗎?」「傻瓜,我能不願意嗎?你年輕,有勁兒,舒服。女人都喜歡大的、硬的。」 後來我在城�參加了工作,叔也帶上嬸母和孩子遷到了遙遠的北方。斷絕音訓一年多後,嬸母又聯繫上了我,每年都以種種藉口來城�和我性交。嬸母說:「你叔說:『你就是去找操去了。』」可他也沒辦法,每年允許嬸母找我一次。 後來嬸母年紀大了,她的生殖器幹澀,性交時她很疼,就逐漸失去性趣了。但我們感情依然如故。 這很不恥,但我不承認這是亂倫! |
- 《菊庭》(未刪節全本)作者:幽欏樺
- 好小孩的日記(一~四)
- 性情記錄1-2
- 乾媽和乾姐
- [經驗故事]墾丁的淫蕩夜
- [學生校園]人妻學妹擦槍走火
- [暴力虐待]少女自虐狂
- [經驗故事]迷路小女生
- [群體換伴]昨晚的三人行
- [人妻熟女]在老公面前發情的人妻
- [人妻熟女]送外賣的熟女
- [不倫戀情]安慰阿姨結果害她懷孕
- [不倫戀情]家庭母子造人運動
- [不倫戀情]繼母與我過假期,好似新婚蜜月妻
- [科學幻想]多啦A夢之記憶面包
- [不倫戀情]撐開妹妹的肛門
- [學生校園]青春的調教(楔子1-3)
- [玄幻仙俠]項羽干琴清
- [玄幻仙俠]仙劍奇俠傳H版 第十一章 蛇妖
- [科學幻想]催眠眼鏡之表姐佳佳(1)
- [玄幻仙俠]令狐沖情慾傳 01-05
- [人妻熟女]人妻Maggie
- [職場激情]黑絲老板娘的無奈
- [科學幻想](變身文 圖文版)絲襪大魔王5—魔法天使
- [人妻熟女]老外大屌
- [人妻熟女]衰鹹濕撲左個靚姐,原來佢4張幾
- [職場激情]最珍貴的生日禮物
- [人妻熟女]和吳姐的性事
- [學生校園]我的女兒和她兩個美麗的女同學
- [職場激情]我的初戀女友
- [人妻熟女]護士服裡的秘密
- [人妻熟女]少婦周冰潔
- [人妻熟女]浮生六戲之當年班花
- [不倫戀情]換女俱樂部Ⅱ 第1-3章
- [職場激情]空姐傻傻愛
- [人妻熟女]奇異的換妻之旅1-4
- [人妻熟女]婆賭氣的一次意外3P
- [人妻熟女]看牙醫的女人(1)
- [人妻熟女]隔壁漂亮的年輕老師雨瓊
- [不倫戀情]脅迫(01~10) (2/2)
- [長篇連載](非原創)風月大陸 第二十七集 (3/4)
- (非原創)風月大陸 第十七集 (3/4)
- [不倫戀情]婆雪兒的換妻經曆(8-10) (2/2)
- [玄幻仙俠]《將軍本色》(全)作者:觀海(先創緋色實體) (5/6)
- [職場激情]我的極限運動 01-06 (2/2)
- [暴力虐待]煉獄天使 1-23集 (完) 作者:半只青蛙&知樂 (3/34)
- [不倫戀情]山村避難記 (5/7)
- [學生校園]黑店
- [附圖小說]看圖說話系列——嫩模2阿遠的回憶
- [人妻熟女]老公和情夫在我家爭奪我小屄的性交權
- [學生校園]上錯廁所找對女友
- [職場激情]新來的總機小姐
- [人妻熟女]中国人,黄色小说
- [職場激情]發現被戴綠帽子我瘋狂地操了自己老婆
- [人妻熟女]我和三個小姨子
- [職場激情]信愛女神
- [不倫戀情]我愛姐姐
- [不倫戀情]家有性變態弟弟
- [不倫戀情]上了親家母
- [職場激情]工棚裡的輪姦
小說區 隨機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