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友站 番號最齊 新作上架最快!(每天更新百部AV)
請使用轉址到網站新介面模板瀏覽, 10 秒后,
会转跳到 ==> https://18av.mm-cg.com
小說名稱:[經驗故事]幹了一位尼姑
文字放大: 自訂文字大小: 行距:|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兄弟在河南東部一個鄉鎮工作,平時很喜歡看書,有些書生意氣。我工作的那個地方有一個叫鄭莊的村子,鄭莊西北頭有一座家廟,是1998年修建的。 現在部分農村有幾個錢了,一些封建設施又沉渣泛起,但人家是經縣宗教局批準的。聽說文革以前就有那麼一座廟,後來破四舊時被拆掉了。 現在為了祈求神佛保佑,鄭莊的幾個搞建築發了財的農民就集資修了個廟。 廟有了,得有住家和尚啊(就是常年住在廟裡操持香火和其他宗教雜務的和尚)。鄭莊的人不知從哪裡弄來一位50多歲的老和尚做住持。但說實話,現在的修行人沒幾個真心奉佛的。由于是家廟,地理又有些偏僻,平時香客很少,香火不怎麼旺盛,和尚也沒多大油水。沒半年,那老東西就找了個理由溜走了,再也沒回來。就這樣一連弄來四位和尚都沒有留住。鄭莊的人也真有辦法,2001年夏天居然弄來了一位尼姑守廟。 我平時喜歡幽靜,喜歡逛廟,所以對鄭莊家廟的發展經歷了如指掌。 2001年7 月的一天下午,我抽了個空騎著摩托車又去了家廟閑逛。 進去以後才發現廟裡居然來了一位姑子。 好象有二十八九歲的年紀,頭皮剃得雪青,身穿一襲淺灰色僧衣,渾身上下收拾得乾淨利落,清瘦而秀氣,正站在廟院裡香爐旁上香。 一見我來。“阿彌陀佛”那尼姑打了個喏。我急忙還禮。 到大殿坐下後,我問她:“釋圓覺師傅呢?”釋圓覺是上一任住持和尚,我和他聊得很好。 “圓覺師傅已經雲游去了。” “哦,請問師傅啥時候來的?” “我來了快兩個月了。”我暗叫慚愧,這一段事情忙,很少到這裡轉悠,居然不知道發生了這麼多變化。 我就和這個尼姑攀談起來。兄弟平時喜歡五花八門的書籍,對佛經也不陌生。 什麼南禪北禪,慧能神秀,大乘小乘,平修密修,我施展開自己博學的知識和伶俐的口才,不到兩小時,那尼姑就對我颳目相看。 最後她說:“阿彌陀佛,我出家近二十年,你是我遇上的第一個對佛經有研究的年輕人。阿彌陀佛,佛祖會保佑你的。” 既然熟悉了,我也問了她一些私人問題,知道她法名叫釋慧元,俗家姓李,原是河南靈堡人,因為十六歲上和母親吵架,一氣之下偷偷離家出走,居然跑到陝西一個尼姑庵出家了。 後來輾轉流離,竟來到豫東地區。 我一看天色不早了,就丟下50元香火錢告辭了。那尼姑感激不盡。 就這樣,我隔三差五地跑到家廟和那尼姑說話嘮嗑。 我們兩人的關系也越來越近乎。 時間一長,我越來越覺得這尼姑有味道。 由于常年不出庵堂不事勞作粗茶淡飯不沾葷腥起居規律心境平和,少世俗之累,無不良嗜好,所以她保養的很好。身量苗條,面色紅潤,皮膚細嫩白皙,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渾身充滿了氣質女人的韻味。我忽然覺得如若和她日逼肯定會妙不可言,別有一番風味。 于是暗下決心要把這女人弄到手嘗嘗鮮。 首先我要打破她對宗教的傳統看法,幫助她去除對戒律的懼心,重新喚起她對塵世生活的渴望。 我說:“你當年出家也有些太草率了,因為賭一時之氣,把一生的幸福都葬送了。”她笑了笑,未置可否。 我看她沒怎麼反駁,繼續說:“按說修行也不錯,不過我覺得你們這種修行的方法太拘泥死板了。” 她微微一怔,說:“施主請指教,” 我侃侃而談:“凡人能否修成正果,根本不在于什麼清規戒律,全在人的一念之間。一念之善可以使人成佛,一念之惡可以使人成魔。只要心中常存一份佛性,多做培根固基之善事,人人皆可以成佛。六祖慧能說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修行全在人心,若修行的人心中不淨,不能去除執著得失名利好惡之心,就是把木魚敲破又有何用?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只要真能做到‘大程心中無妓’,什麼喝酒吃肉,飲食男女,那都是俗人眼中的罪惡,真正的得道者是從不忌諱的。濟公和尚天天吃狗肉,少林寺的武僧一千多年來也沒怎麼忌口,不照樣修行得道?同是佛門弟子,難道佛祖還會兩樣對待?心中有佛,身外無物,即使在俗家人眼裡淫穢不堪的西藏密宗的男女雙修其實也是四大皆空,那才是真正的上乘境界。如果整天拘泥于清規戒律,敲魚念經,刻意地回避這回避那,表面上好象很虔誠,實際上是心中不淨,心魔在作怪。我看這才是墜入了魔道。” 她笑了:“看不出,你到挺會勸人的,不過你說的也有幾分道理。只是我們出家人真要那麼做就有些大不敬了。” 我看她已經有些動心,繼續開導她:“李姐(我故意不叫她師傅),佛曰: 一切有為相皆為虛妄。實際上對任何事情,哪怕是戒律,如果執著心不去,都是魔道。〈〈壇經〉〉上也說,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是最大的修行。修行其實是一件很實在的事情。刻意地與世隔絕,人為地封閉自己,並不是什麼虔誠。〈〈西游記〉〉中的豬八戒好吃懶做又凡心不褪,最後不照樣修成正果?佛家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看來佛祖也是提倡入世修行的。並不主張脫離人間煙火,一味追求空靈什麼的。” 她聽到這裡猛然抬起頭來:“依你看,該如何修行方為正道?” 我說:“很簡單,象正常人一樣生活,該乾什麼就乾什麼。既不要刻意地追求,也不要刻意地回避,保持一份平常心和善心。只要心中常存佛性,因緣來到,佛祖自會來接引。” 她眼神一亮,隨即又暗淡下去,口中喃喃:“唉,象我這樣的年紀還能有什麼正常的生活?” 我一看有門,急忙勸她:“李姐,你才不過三十多歲,長得又漂亮,正是青春年華,我看現在開始絕對不晚。”她聽後臉上飛起兩片紅雲,隨後長嘆一將近二十年的時光,急切之下難以改變心境。 于是叉開話題,給她講了不少生活趣事,逗得她一陣開心後就告辭了。 回去後,我托朋友弄來女用助興春藥,據說很有效果。 過了一個星期,我特地選一個傍晚又去了家廟。 到達時,她正在念經,見我到來非常高興。 我拿出在縣城買的一串佛珠項鏈和一身藏青色的秋衣秋褲送給她,她稱謝不已。 我們兩個在她住房裡說了一會話。 我假裝口渴,趁她去廚房倒茶之際,迅速地將藥面倒入她喝水的口杯中,然後又若無其事地坐在原位上。 她倒水回來,我們繼續聊天。 我告訴她前幾天出了一件稀罕事。 她一邊喝水一邊問是什麼事。 我告訴她劉莊一馮姓村民扒灰把自己的兒媳婦領跑了,現在他兒子正在家尋死覓活呢。 見她聽得津津有味,我故意把一些細節尤其是那兒媳婦的風流韻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十幾分鐘後,我發現她面色越來越潮紅,神情也不自然了,知道藥力發揮了作用,故意講得更起勁了。 又過了一會兒,我見她雙手在身上上抓下撓,眼神也有些迷離了,喘息也不均勻了,顯然方寸已亂,故意問她:“李姐,你怎麼了,不舒服?” 她口中含混不清,“嗚嗚”地不知怎麼說才好。 我說:“要不然我扶你進屋休息吧。” 她剛要拒絕,我一步竄到她跟前,一只手抓住她的胳膊,一只手扶住她胸肋部,把她拽了起來。 她“恩”了一聲,就側著身子半斜在我懷裡。 我緊緊地摟住她,慢慢地往裡屋床上挪。一路上我故意不停地變換手法,把她胸前身後摸了個遍。 她也顧不得許多,一只胳膊居然繞過我脖子後面,緊緊地靠住我,身子軟得象一只水母。 我把她攙在床上,說:“我給你按摩按摩吧。”不等她拒絕,我的雙手就在她周身游動起來。 我看她嘴唇動了動,但終于沒有說什麼,慢慢地閉上眼睛。 我輕輕地揭開她的僧衣,發現裡面還穿著小褂,又把小褂揭開,露出光潔雪白的皮膚。 她乳房不大,但十分的堅挺,一點也沒有下垂的跡象,紅紅的奶頭象一粒熟透的櫻桃,我看得熱血沸騰,上去一口噙住乳頭,使勁地吮吸起來。 她受到刺激,吃了一驚,努力地睜開眼,口中喃喃地說:“別,別這樣”。 我說:“李姐你就別折磨自己了。”我撥開她無力的雙手,摟住她光滑的身體,用嘴堵住她的嘴唇,一只手解開她寬松的褲子,一把擼到膝蓋下面。 她驚得坐了起來。 我不容她反抗,雙手提住她的腳脖往上一掀,她的上身又被摜倒在床上。 我貼住她光滑的屁股,掏出早已堅硬的雞巴抵住穴門,挺身就刺。 沒想到她從沒經過性事,陰道非常乾澀,而且連逼門也很小,我只好吐些唾沫抹在逼上,又把雞巴也潤滑潤滑,使勁一頂,她“唉吆”一聲,我低頭一看,雞巴已攮進去半截。 她剛才還亂抓亂搡的,等感覺我已經攮進去了,反而安靜了,雙手捂臉,一動也不動任憑我動作。 我先慢慢抽送,等感覺比較潤滑了,才俯下身去,用嘴輕輕地吻她的胸膛,乳房和額頭,同時迅速地抽動著陰莖。 我摟起她的身體緊緊地貼住我的胸膛,她慢慢地把手伸到我的背後,死死地扣住。 我更加賣力了,這時她的逼裡已經比較的濕潤了,我趁機放開架勢大肆攮進拔出,我用手在她滾燙的身體上到處游走。 她的肌膚果然十分的白皙光潔,象綢緞一樣。瘦俏的體型很是性感。 我每一下的衝刺都能達到最深的頂點。 溫暖的逼肉緊緊地環繞在陰莖周圍,讓人感到一種包圍和緊握。 她顯然也被我強烈的刺激弄得動情了,哼唧不已。 我又用手撫摩她光滑的頭部和清秀俊俏的面龐,把舌頭頂進她的口腔裡來回攪動。 她一開始還有些反抗,在我激情的衝擊下漸漸地放開了,身體也配合了動作。 我知道只要這次把她弄得死去活來,以後就可以長驅直入了。 于是我閉上眼睛,不再看她讓人興奮的肉體,同時把心思集中在過去的一些讓人不愉快的經歷上,盡量地延長高潮的到來。 當我發覺就要到終點站時,就拔出陰莖,在逼門外邊稍事休息後再行作戰。 就這樣堅持了二十多分鐘,我發現她已經虛脫了,陰道裡的肌肉已經抽搐了不知道多少遍。 我睜開眼睛,連摸帶親,讓興奮迅速地到達頂點,同時把力量加到最大。 她白嫩的軀體在我猛烈的撞擊下快要散架了,在床上象面團一樣被我揉來搓去,一點力量也沒有,嘴裡發出模糊的哭泣般的呻吟聲,已經進入恍惚狀態。 我心裡一陣激動,一股酥癢酸麻的感覺從大胯處升起,我急忙把陰莖緊緊地頂住花心,隨著陰莖一陣劇烈的抖動,一泡精液一滴不剩地射在陰道深處。 她感覺到我射精後,忽然緊緊地捂住臉,輕輕地抽泣起來。 我有些害怕了,輕聲地問:“姐,你生氣了?” 她聽後睜開眼睛,紅著臉說:“你叫我以後怎麼做人?” 我看她不象惱怒的樣子,放下心來,嬉皮笑臉的說:“不做人不能做神?” 她“噗嗤”一笑,隨即幽幽地說:“哎,我早看出你不是個好人,可我就是不能拒絕你。你真是我命裡的克星,我的魔鬼。” 我一陣激動,脫掉了自己的衣服,上床摟住她又親又啃,一直弄到凌晨四點才悄悄離去。 就這樣,我隔三差五地去家廟過夜,和釋慧元的感情也越來越深。 直到農歷十一月的一天,我去了家廟,發現她已經不在了。詢問周圍的群眾才知道她已于兩天前不辭而別,留下一張紙條說她有急事要辦,估計不能回來了,叫不要等她了,再尋一位住持師傅。 我怏怏而回,過了幾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打開一看才知是她寄來的。 “我走了。我不想自己更難過,更害怕你挽留乞求的眼神會動搖我離去的決心,所以沒有告訴你。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已經沒法再修行了,決心蓄發還俗,生下這個孩子。但我不會結婚,孩子就是我一生的希望和依靠。等他(她)長大了。我會告訴孩子關于你的一切。但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是沒有希望的。雖然我有些恨你,但我更感謝你帶給我的快樂,感謝你把我重新帶入這個活潑潑的世界中來。將要離去的時候我哭了整整一夜,我發現自己是那樣的愛你。如果再不走,我擔心會控制不了自己,會給你帶來麻煩。我不願意你受到任何指責和傷害。 所以我只有選擇離開。再見了,我的愛人,我永遠想念你。祝你永遠幸福。元字即日” 我的淚水一下子奪眶而出,久久地不能平靜。 |

- [經驗故事]玉女裙下的秘密
- [科學幻想]風采女孩選拔大賽
- [經驗故事]遊覽車抽插
- [學生校園]誘姦一個19歲大學生的經曆
- [經驗故事]酒後失身
- [經驗故事]開情趣用品店的好處
- [經驗故事]年輕縣委書記的性愛經歷
- [經驗故事]網咖的洗手間
- [職場激情]美艷的護士做炮友
- [學生校園]超級淫蕩女高中生
- [不倫戀情]女友家的亂倫
- [科學幻想]春夢
- [人妻熟女]老婆員工旅遊
- [暴力虐待]電車肛辱
- [不倫戀情]幾天不停的跟親姊做愛
- [職場激情][轉載] 斷了腿的小女生
- [經驗故事]帶醉倒的Susan去爆房梅開二度
- [不倫戀情]我和姐姐被迫的性事
- [職場激情]異地女友(28~29)
- [職場激情]親愛的鄰居
- [職場激情]母女的顫抖
- [職場激情]隔壁的怨婦人妻陳太太(隔壁的陳太太)
- [人妻熟女]小夫妻
- [職場激情]學姐跟男友
- [職場激情]激情遊戲
- [長篇連載]伊甸園之奴寵戰紀 13-14
- [職場激情]惡魔少婦之元旦故事
- [職場激情]我的專屬小淫娃
- [不倫戀情]蝕骨銷魂屄 (2/3)
- [玄幻仙俠]【九流術士】第二部 (11-20集) 作者:Michanll&英雄 (8/34)
- [人妻熟女]【我的嬌妻洛靈】(1-5) (2/2)
- [玄幻仙俠]【半步多欲望傳說Ⅰ】作者:骷髏精靈&阿苦 (14/18)
- [不倫戀情]我和娘(1-5) (2/2)
- [經驗故事]獵物
- [職場激情]風流小皇帝(01~19) (3/5)
- [不倫戀情]百貨公司的亂倫
- [不倫戀情]與岳母及小姨子偷情
- [經驗故事]小美女
- [職場激情]女友在醫院的遭遇
- [人妻熟女]與導遊阿姨的真實經驗38-45
- [經驗故事]上了15歲小妹
- [不倫戀情]心底的悔恨,血淚的亂倫
- [科學幻想]女惡魔人外傳芬芳染血
- [人妻熟女]紅塵倚天尋美錄(01-40) (1/3)
- [暴力虐待]瘋狂輪姦
- [職場激情]美少女春意融融
- [人妻熟女]被老公出賣而成爲他人女友的淩兒 (1/2)
- [職場激情]辦公室的淫婦
- [人妻熟女]老婆醫院失身
- [玄幻仙俠]醉紅情
- [職場激情]極樂超商
- [人妻熟女]酒後人妻
- [學生校園]學姊的呻吟聲
- [職場激情]雙妹被輪姦
- [職場激情]找女友卻找到了淫娃
- [不倫戀情]迷人又漂亮的大嫂
- [人妻熟女]當兵真實經歷
- [人妻熟女]吞精的良家妻子
- [暴力虐待]亂七八糟之淩辱女友
- [職場激情]清純女友庭芳
小說區 隨機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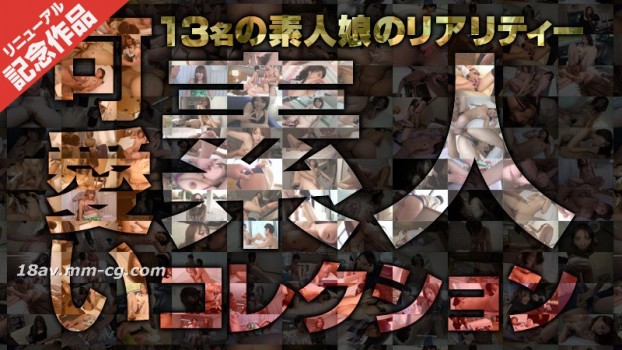






![Bejean On Line 2008-01 [Panty]- Nana Aoyama](https://fchost1.imgstream2.com/s/wp/wp14163.jpg)




